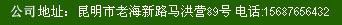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北京专业的白癜风医院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万氏祠堂 我父亲进四岁那年的季春,黄歇街五百年来的第二间私塾在万氏祠堂开学了。这本是件大好事,却引起全街的震动。 何以如此?这得要从街上的姓氏说起。 街上住的两千多人只有三个姓氏:万姓、李姓和谢姓。早先有句顺口溜,说的是三个姓氏曾经的位势:“万半头,李半截,谢家中间打个楔”——万姓住上街,李姓居下街,万李各占半壁江山,惟谢姓独门独户插在中街。 李姓据说为原居民,万姓明初从江西迁来,谢姓也来自江西,却是在清末。万姓初来乍到时,才三十来户,人数勉强够李姓的零头,但事事受李姓人的关照,连李氏祠堂的私塾对万姓也是敞开大门的。为此,万姓人普遍对李姓心怀感激,与李姓人处的甚是和睦。 扎根黄歇三十年后,万姓人在上街顶头盖起了万氏祠堂。自那时起,除了祭祀先祖、婚丧寿喜、族训教化、族人纠纷及违规惩处等族内事项,街上的所有公共事务,诸如应对衙役、交粮纳税、扶危济困、赈灾施救、管理街市,调解街坊摩擦、操办端阳节划龙船及其他公共活动,一向都是万李两家祠堂协商处理的。再加上两姓之间你娶我嫁,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五百多年来,街上虽不乏鸡毛蒜皮的口角,却从无大的纷争,氛围堪称和气、和平、和谐。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自晚明起,万姓人丁兴旺,家家户户每一代都生有几个男伢,少的三四个,多的六七个;李姓则刚好相反,星火寥落,好几年也生不了一个男伢,甚至大多数人家数代都只有女无儿。没等到清中期,万姓人就占了大头,不仅上街清一色姓万,下街也扎进去几近半成。李姓人为此惶惶不安,风水先生走马灯似的被族长请来,这个说李姓先祖未葬在旺男丁的风水宝地,那个怪万氏祠堂盖得比李氏祠堂高……族人们也竞相四处求医、散财、求神拜佛,或纳妾添房,各种法子使尽,李姓人丁不增反减的势头仍然遏制不住。 更为诡异的是,在明清两代,虽然黄歇鲜有兵燹之祸,但每一次的洪涝、旱灾和瘟疫(史料显示,仅明清两代,黄歇所处的湖区,共发生过六次大旱灾、两次大洪涝和二十次瘟疫,死者无数),总是李姓男女老少殁的多,仿佛是上苍要灭李族似的。及至清亡前夕,李姓已不到十户,人口不足三十,且老弱病残的居多,李氏祠堂坍塌在野草丛中,李家人的良田、房屋及店铺也陆续落入万谢人家。 谢家的人丁也是寂寥得稀奇。我曾祖父在黄歇扎根后,两代单传岂不说,到我父亲三岁那年,上苍给谢家做的减法近似邪乎,竟然只留存下他们父子二人。曾祖父遗留的家产——小半条街的交易行、数百亩良田和几栋大宅小屋,我爷爷竟日拿它们泡在赌场做除法,到他的独子六岁时,终于把那大一份遗产做到了他人名下,留给我父亲的仅剩一栋最小的祖屋…… 李姓的衰败零落与谢姓的孤灯冷烟,使万家的人陷在迷信的深渊里自得其乐,他们常常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说黄歇是万家的万福之地。 自然,万氏祠堂就成了黄歇街惟一的祠堂,除了万姓族内的事情,街上的一切公共事务,包括李谢两姓及方圆十里来来往往的外乡人所生之事,自此都是万氏祠堂说了算。 虽然万姓人多势大,万事都是万氏祠堂做主,街上却并未出现万姓人横行霸道,或李谢二姓及外乡人受欺遭凌的现象,秩序一如从前那般和平和谐。 这不得不归因于万氏祠堂治理有方。 原先,万氏祠堂当家作主的仅族长一人,族内生出的事如何裁决和处置,绝对是他说一不二的,族人们从无任何异议。自李氏祠堂荒废后,族长因担心如日中天的万姓族人仗势欺人,进而为非作歹,便在族内选出十五位广为敬重的中老年族人,作为祠堂尊长协助他治理族内和街上的事务。 尊长被赋予了两项职责,一是每个季度召集万姓的后生子在祠堂做一次族规族训的教化,尊长们轮流跟他们讲万姓先人遵规守训的往事;二是参与祠堂对所有事情的裁决评判。十五位尊长涵盖了万姓各房,称得上各个支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威望、正义与齐心织起一张大网,把族里的后生子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再加上各家家长对子女平日里的耳提面命,万姓的后生们几乎个个都规规矩矩,没人敢惹是生非,寻衅滋事的。除此以外,祠堂在筹划每年的清明祭祖、婚丧寿喜和端阳节龙舟赛等活动时,族长总是把后生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担起责任,发挥作用,得以成长。近三十年来,但凡街上出现扯皮的事,不管是万姓族内的,还是万姓人与李谢或外乡人之间的,族长都会将十五位尊长请到祠堂进行评议,把握的原则是对万姓不偏袒不护短,对外姓不歧视不轻贱,一碗水端平,公平处置,每每使涉事各方心服口服。因此,万氏祠堂在黄歇周边一直享有很好的口碑。 话说是年正月十五过后,万姓因老族长年老体弱换了新族长。新族长名叫万作仁,四十六岁,人高马大。推选他当族长,万姓族人居然没一个不同意的。老族长甚是欣慰,说,作仁得“大满贯”一点也不奇怪,他是街上最合符当族长条件的人,真正称得上众望所归。 老族长所说的“当族长的条件”,是兴建万氏祠堂并推选首任族长时定下来的,一共有四条。即:家族成年男丁人数须较多、为人处事须公道能干、本人家境殷实、须年过不惑而且身体健壮。除了这四个条件,当时一同定下来的还有族长推选办法,叫作“三步走”:第一步、由万姓德高望重的长辈在祠堂推荐人选,获得多数人认可的,才能确定为新族长人选;第二步、长辈们在祠堂听取被推选人的意见,考察他是否愿意并怎样为族人做事;第三步、召集全体万姓成年男丁在祠堂门前集会(族长被推选人不得到场),向大家介绍被推选人情况,多数人举手同意即为通过。若举手的人过不了半数,则须重来一次“三步走”。不过,重复“三步走”的事从未发生过,以前的历任族长推选人皆获得过多数人的同意。 惟有新族长万作仁是个特例。他创了万姓族长推选史上的两项记录:一是全体长辈不谋而合地推举他,二是万姓成年男丁全都为他举起了手。街上的人把这叫“大满贯”。确如老族长所说,他当族长是众望所归。他不仅符合祖先规定的当族长的四个条件,还比历任族长多出了一条。其一,他在六个弟兄中排行老三,他自己有五儿一女和八个孙子,包括他父亲和弟兄们在内,他家四代人中共有六十六个男丁。在重男轻女的黄歇,家族男丁多,不光面子大,更重要的是腰杆子硬,说话底气足,没人敢不听;其二,他为人孝顺、厚道、正义、开明、小意(小意:黄歇土话,即“谦恭”意思)、大方,在族人中素以处事公道出名;其三,他家富裕,水稻种了近百亩,杂货铺也开的风生水起;其四,他正当壮年,扛一百几十斤的谷袋子轻轻松松,有能力也有精力为族人和全街做事。多出的一条是,他家家教传承极好,男儿人人孝顺正派,女子个个贤惠勤快。 时隔五十多年后,我从希伯嘴里听到“三步走”和万作仁的名字时,惊叹得目瞪口呆。“这不就是我们大学老师讲的民主吗?”希伯对我的回应却是淡淡的,“差不多是吧。”他伸出右手,捋了捋稀疏的八字胡,“呵,我们的先人虽然是泥腿子,没上过学堂,可聪明得很,特别是当族长的,都是有头有脑的明白人,一点不比现如今的大学生差。” 新族长万作仁果然不负众望,甫一上任就办了四件让全街人叫好的事:发起修订万氏族谱、帮扶万李二姓的四户贫寒人家、在街上竖起四块族规石碑和扩大祠堂公田并确定责任人。 万氏族谱每二十年修订一次,此次修订实为续谱,要将新一代的万姓男丁增补进谱。依照常规,作仁族长先是邀请尊长们商议修谱事宜,众人赞修谱为千秋功德,一致同意。修谱之事议毕,有三位尊长提出,应该将作仁创推选族长的两项记录记载在族谱里,以激励后生。话音刚落,即遭到新族长的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修谱修的是全体族人的根脉,不是我万作仁的个人荣光榜,这事万万不可!要是坏了规矩,以后就麻烦了。见他说的在理,三位尊长只得放弃提议,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通过这事,大家对万作仁更是敬重。次日,新族长率先捐钱,三日之内,祠堂就收齐了修谱所需的全部银两。随即,作仁族长指定了上过私塾的四个族人来修谱。这四人都曾在李氏祠堂读过私塾,虽然上的时间最长者不过三个月,充其量只能算识文断字,可他们毕竟是族人中的全部读书人。 街上有四户特别穷困的人家,其中万姓一户,李姓三户。万姓的那户只有父母和儿子三口人,父母长年生病,已丧失种田能力;独子叫万述侯,从小娇生惯养,十九岁了仍不肯下地干活,成天游手好闲,东混西荡,无所事事;房屋也因多年失修,瓦破墙裂,透风漏雨。这种人家,在万姓绝无仅有。街上有句流传已久的俗话:“不怕贫穷,就怕懒虫。”因此,好吃懒做的万述侯很是被族人看不起。李姓三户都是有女无子,且姑娘们幼小,父母不是残疾就是体弱多病,日子过得清汤寡水。此前,这四家一直靠亲戚周济,但穷困像树根,接济如施肥,受的接济越多,穷根反而扎得愈深。作仁族长特地召集家境富裕的族人和十五位尊长专门商议此事,出的结果是:对四户的帮扶不分姓氏,一视同仁;要从根子上帮他们摆脱困境。具体的帮扶办法为:征得他们四户的同意,由祠堂作价并出资购买他们的部分农田,以补充祠堂公田;按照四户的每家人口,由祠堂每年给予他们口粮补贴;将他们的成年后生安排到祠堂做事。四户人家无不欢喜。 四块族规石碑从选料、刻字到选地,只用十来天时间就竖起来了,分别立在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棵老樟树下面。每块碑上刻有十二条万氏族规,内容为:敬祖宗、敦孝悌、睦宗亲、尊师长、励忠节、笃信义、恤孤寡、肃闺门、倡勤俭、承祖业、息争讼、绝邪风。 万氏的族规族训是先祖从江西带过来的,先前和李氏族规族训一样,也是一直挂在祠堂,由家家户户世世代代口口相授。如今把它们刻上了石碑,且竖在人多显眼之处,人们感觉很是新鲜,每天都有一拨人围着石碑或坐或站,有的年长的族人还把手放在冰凉的石碑上,从上到下又自下而上地摸个遍,那神情,俨然年少时聆听父辈的谆谆教诲,尽管他们没一人识得碑上的字的。 从内容上看,万李二姓的族规族训几无差异,看重的都是孝悌、忠义、礼节、良善、互助、勤俭、正气……等等。族规族训的具体内容,虽然没几个人能说得清讲得全,但经过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早已潜移默化得像播在男女老少心里的种子,牵引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除了口口相传的教化,万李两家祠堂对族规族训的严苛执行,于扬善抑恶功不可没。街上人把祠堂司法叫作“行家法”。但凡族人做出有违族规族训之事的,概由族长、族尊和涉事人的家长坐到一起裁断,继而在祠堂予以处罚,然后在街上鸣锣广而告之,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譬如:对撒谎骗人、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或短斤缺两等行为的,在族人的监督之下,或由家长在祠堂劝导,或由族长在祠堂实施严厉训诫、罚跪和掌嘴;对违背人伦道德、行伤天害理之事的,如不孝不贞、欺行霸市、作假行骗、恃强凌弱、为富不仁及亵渎神灵等,一律在祠堂进行罚款罚物,或严加鞭笞;对上述违规行为极其恶劣或屡教不改者,则实行逐出族门甚至沉湖溺毙。 “逐出族门”与“沉湖溺毙”是祠堂家法中的“极刑”。前者以褫夺血缘赋予的姓氏权且斩断父系血亲关系来严惩违规人,使其失却庇护,“六亲”不认,流离失所,无依无靠,活得像孤魂野鬼;后者则是以古老而无情的手段,对违规者的生命快速灭绝,使其从鲜活的族群中消失得干干净净。“极刑,是对无可救药的极劣或极恶之人的极端严惩,同时也起到令族人终生不忘的严厉警示,从而使祠堂更具威严,族规族训刻骨铭心。 五百年来,无论李氏祠堂还是万氏祠堂,都未曾动用过“逐出族门”的家法。这是因为,长期的家庭教化与祠堂“家法”的约束,使得街上的人养成了友善、诚信、敦厚、尊老爱幼、路不拾遗和互帮互济的淳朴民风。 但“沉湖溺毙”的家法,李万两家祠堂却各行过一次。 李氏祠堂的“沉湖”家法是在明朝中期行的,沉掉的是一个当土匪的二十岁族人。那年轻人一天半夜到附近湾子的富户人家打劫,竟然还强暴了一户贫寒人家的十五岁哑女。祠堂沉毙他的理由是:年纪轻轻不行正道,既当土匪又残害良家女伢,悖人伦逆天理,作恶至极,是李氏的败类,该天打五雷劈。祠堂替天行道,以儆效尤。“沉湖”的第二天,祠堂还以“子不教父之过”为由,对“败类”的父亲予以严厉责罚。街上的人无不拍手称快。据说,这次“沉湖”事件威慑力极大,从此以后,街上再也没出过当土匪的人。又据说,“沉湖”过后四天,先后有两股土匪派人带话给李氏族长,说辞都一个意思,即:被沉掉的人不是自己这边的,而是属于对方一伙。这是我高中毕业后从希伯嘴里听到的最早的“甩锅”故事。 万氏祠堂的“沉湖”家法则是三年前施行的,希伯记忆犹新。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三伏天,我父亲尚在蹒跚学步,自然不可能亲临现场观看。他晚年跟我说起这事时,分明是希伯讲古的口气,说那次的家法把万姓的女人吓得好久不敢吱声,不敢出门,也使得希伯痛下决定立了大志。 希伯那年八岁,他说他挤到人群前面,目睹了沉湖家法的全过程。 被沉湖的是个年轻女子,蛮标致,二十二岁,叫李小娥,娘家在下街。她父母只生了她一个,拿她当儿子养的,嫁了她没几个月,他们就过世了。她是十五岁嫁到上街万姓人家的,进了洞房才晓得男人长期肺痨。男人大她两岁,呼吸跟猪打鼾一样,人瘦得比鸦片鬼还不中看相。半年不到,那男的就蹬腿闭眼了。才十六岁,花一样的人儿,就要守寡,亲人也没一个,这叫什么命啊!好在婆家厚道,老少十几口人,没一个刻薄她的。婆婆真的是拿她当亲姑娘疼,不过对她也盯得很紧,除了让她清早去河边洗衣服,其他时候轻易不准她出门,毕竟她花苞初开,生怕她做出对不起祖宗的事。呵,见了鬼,千疼万盯,她还是偷人了。 发现这事的,是你们谢家交易行的一个伙计。交易行代店铺订的货,向来都是天蒙蒙亮就送到的,但那天太阳快一竿子高了,余家埠的船工还没把货送到。伙计急了,就跑到小河边去找。船在码头,货也在船上,独独不见船工。于是伙计就敲锣行街,呼唤那船工的名字。喊到稻草捆堆成山的地方时,突然见那船工的人影从草堆洞里飚出来,像射出的箭飞快朝河边跑去,草屑子在他身后纷纷扬扬。没等伙计晃过神来,又见到一个年轻女子从草堆洞里钻出来,右手夹着腰里的一盆衣服,左手在拣身上的草屑,慢悠悠走到他跟前,看了他一眼,说:“小心把你的眼珠子瞪掉。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人家没关系,我现在就去祠堂。”说完就往街西头走去。 好侠气的女子!伙计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忍不住在心里赞叹…… 第二天上午,万氏祠堂就出了裁断结果:寡妇失节,今日沉湖溺毙。祠堂还派人敲锣游街,郑重通告这一结果。 行“家法”的时辰选在太阳犹犹豫豫西沉之时,地点是街北面的湖边。 湖畔的一排柳树雕塑般纹丝不动,空气火烫似的使人感到气短胸闷。但那里已站满万姓族人,其中女人差不多占了一半,是族长特地派人通知她们到场的。 人群围着一个六尺长两尺高的篾篓子,篓子下面绑着一大麻袋砖块和石头,离篓子不到两尺的岸边靠着一条木划子。 寡妇穿戴一新,双手用麻绳绑在背后,由两个年轻人押到湖边。 走到篓子跟前,寡妇站住了,闭上双眼,面无表情。 人群鸦雀无声。 族长朝那两个年轻人做了个捏拳的手势,那两人立即把寡妇扳倒在地,一人抬肩,一人托脚,将她塞进篾篓,然后扣上她脚头的篓门。寡妇从被扳倒到送进篓子都一动不动,直到篓门被扣上才睁开眼睛,环视人群。看见人群中的婆婆后,她突然大声地嚷了几句:“婆婆,你们对我的好我记得。不要怨我给你们丢人!我宁愿去喂湖里的鱼!” 这是街上的人第一次听见寡妇的声音,也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她的声音干脆、响亮,没有一点恐惧和哀伤,我听得心里直发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人群一阵骚动,但没人出声,连树上的蝉鸣也戛然而息。 族长又做了个挥动的手势,人群中马上走出四个壮实的男人,他们和那两个年轻人一起把篓子抬上了木划子。四个壮汉下来后,船还被压沉下去半截。 船工把船缓缓划到两三丈远的地方后停下。只见两个年轻人用手抄住装石头的麻袋,大吼一声,一把将篓子掀进了湖里。 人群中突然爆出女人的尖叫,接着出现低声的抽泣。 湖里激起一阵阵波浪,把船颠得摇晃起伏。 篓子很快就没进水里。湖面上先是冒出串串泡泡,接着化出一个又大又深的漩涡…… 寡妇的婆婆走到篓子上船的地方,弯下腰点香烧纸。 这时响起了族长的声音,“女人不贞,败坏族风。行家法是为了正族风。男人要行正道,女人要守妇道。祖宗定的族规,大家千万要记住啊!散了吧。” 人群散尽后,希伯还站在湖边,盯着篓子沉下去的地方发呆。这么标致的年轻寡妇,只因为“偷人”,说沉就沉掉了,这哪是人做的事啊!老子要发愤读书,这辈子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沉湖”过后,街上的人闭口不谈寡妇,就连那些平日里爱嚼舌根的女人,私下里也没人议论她是怎么跟那船工好上的,尽管她们很想知道。 余家埠的那个船工,从此再也没来过黄歇街。 扩大祠堂公田并确定公田责任人,这事尤受族人称赞。祠堂公田归属祠堂,由族人轮流耕种,每年产的稻谷拿去换钱,用于祠堂的各项开销。公田以前只有八亩,在万姓人少的时期,收益还勉强够用,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祠堂的开支项目越来越多,公田的收益显然严重地入不敷出。如果再像前几任族长那样,动不动就找富裕族人化缘,肯定是难以行通的。现在好了,新族长在解决贫寒户的同时,把公田扩大到六十多亩,还指定了万述侯等三个族人负责耕种的管理事务,祠堂的收益终究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族人们无不觉得新族长办事有头脑有眼光,是个了不得的人。 然而,族人们怎么也没想到,扩大祠堂公田这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族长另有深意。直到阳春三月的一天,作仁族长召集尊长们到祠堂商议大事,大家才恍然明白过来。 那天上午,全族十五位尊长应邀到祠堂议事,族长早早就恭候在门前,满面笑容,双手合十,说是请各位先好好观看修葺过的祠堂。 祠堂位于上街西头,与土地庙并排,白墙黑瓦,实木结构,三重进深,“万氏祠堂”四个墨色正楷在门楣上方格外醒目,大门左右各立着一尊石头狮子,门前是一个五亩大的场子。 族长指着土地庙对尊长们说:“各位尊长,听老人们讲,当年是祠堂先盖,土地庙后建,所以特意把土地庙盖得比祠堂高。为么事要这样做呢?为的是让土地爷保佑我们万家子孙在黄歇平平安安和兴旺发达。” 众人听罢一头雾水,这缘由我们早先就听老人们说过了,为么事今天要讲这事呢? 接着族长抚摸着漆得簇新的大门发问说,“各位尊长,这两扇大门,新的好看,还是旧的好看?” 当然油漆一新好看啊,这还要问?族长今天怎么了?众人疑虑重重,不过没人吱声。 不等尊长们开口回答,族长紧接着又说:“祠堂门口的这两头石狮子守了五百来年吧。”两尊狮子洗刷一新,族长手抚着一个狮头自言自语道,“我一直在想,它们在祠堂守什么东西?” 大家一下懵了。这是个么意思?族长今天要搞个么名堂?他是不是有毛病了?但还是没人出声。 说到这,族长躬身把手朝大门里面一伸,“各位请进!” 族长最后进屋,却快步走到大家前面,只说了一句“请各位仔细看看祠堂”,便不再吭声,径直向里层走去。 尊长们慢走细看,发现祠堂里面该粉刷的地方粉刷一新,该修补的地方修补齐整。祠堂自建好后一共整修过六次,这回算是第七次。进门后的议事厅宽敞明亮,桌椅板凳摆放的齐齐整整。过了议事厅便是天井,打扫的干干净净,六株栀子花绕着那棵四百多岁的樟树,一看就是新近栽的。穿过天井进到中庭,左侧也摆上了十几张条桌和条凳,右侧用屏风隔出了一个小间,放着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木靠椅。整个中庭通透光亮,原来是屋顶上新添了六片亮瓦。再往里走便是万氏祖先牌位,到处擦拭得明净光亮。祖宗牌位梯次陈列而上,显得整齐肃穆;龛案正中摆放着一个香炉,缕缕香烟袅袅升腾,香炉两边各自排列着十八盏棉籽油灯,将层层叠上的祖先牌位映得红光熠熠。 族长笔挺地立在祖先牌位左前侧,把目光从牌位移向大家,说:“请各位敬拜祖宗。”说完,他带着十五位尊长齐齐地跪拜在蒲垫上作揖磕头。 拜毕祖宗,族长请尊长们回到议事厅。待大家坐定,他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说:“各位德高望重,本人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各位商量一件大事。” 众人张嘴盯视他。 “我想开一所私塾。”这句话,族长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的。 “啊!”众人惊讶万分,谁也没想到族长搞的是这么个名堂。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接着便七嘴八舌地开腔了,但说的全是反对的理由。 这个说,五百年前李家就在他们祠堂开过私塾,我们万家的人也在那里开蒙。办得怎么样?那么多代人下来,街上的学生拢共也就几十个,除掉死了的,现在只剩下我们万家的四个活宝,没出过一个秀才。教书先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都是外乡请来的。黄歇街自古就没有读书的风气,办私塾肯定是竹篮子打水! 那个说,族长,你是不是觉得黄歇人不读书就活不下去了?是的,万家的人的确没几个能识字的,可是家教都严得很啊,人人懂礼节讲诚信守本分,一家有难大家帮,孔老夫子编的《三字经》《弟子规》哪个家长不会背几句?还用上私塾吗?再说了,你族长不也没上过私塾,这族长不是当的挺好的吗? 还有的说,我最见不得读书人,他们开口就是之乎者也,做人做事没一个安分的,喝了几滴墨水就想往外跑。要是人人都上外头去野,黄歇以后还有么子搞头?出去又能搞个么子大事?照我看啦,他们不是怪物就是废物,眼睛都长在头顶,就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看看我们万家那四个上过私塾的,哪一个把田种的比我们好?把铺子开的比我们强?黄歇人祖祖辈辈种田打鱼开小铺子,只要认得银钱,通情达理就行了。 有几人附和说,对啊,没有私塾,没有读书人,照样种得好田,开得好铺头。族长,你再想想清楚,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花钱开私塾。 …… 待他们说完,作仁族长笑了笑,说:“你们到底是尊长啊,说的都在理。”他顿了顿,两手十指交叉,“这样吧,先前我问的几个问题,现在请你们答一答。” “祠堂门是新的好看还是旧的好看?” “肯定是新的好看啊。我们又不是苕货,这还不晓得?” “那就对了,门是新的好看,人应该也是新人有盼头有奔头吧。什么叫新人?照我看,是读书读得好的才叫新人。” “那一对石头狮子守了几百年,守的是么子?” 没人回答。 “那我就不客气了。”族长稍稍提高了嗓门,“我琢磨啊,狮子守的是比我们有出息的人。田我们种了几百年,鱼打了几百年,铺头也开了几百年,可我们跟祖祖辈辈一样,到而今连监利的地界都没出过,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几大,我们没一个晓得的。”说到这,他双手一摊,“歌不会唱,舞不会跳,字认不到一箩筐,对我们这些老朽来说没么事,但我不希望万家的后人还跟我们一样。我的话虽不中听,但是心里话。” 族长有点激动,声音开始变得低沉,“我算了算,而今,街上的后生子将近一千五百个,这不是个小数字。他们将来做么事,我们当长辈的是不是要操操心?再者,你们也看到了,这些年世道变的快得很,要是后生们还跟我们一样,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只晓得守着几亩田、一把渔网和一个小铺头过日子,我看以后是要出麻烦的,黄歇也怕是还要闭塞几百年。” 他话音刚落,老族长就接过他的话头,问:“作仁啊,你刚才说的还真是个问题。我问你,后生们以后会出么样的麻烦?跟我们说说看。” 族长挨个看了看每位尊长,慢吞吞地说:“到底会出么子麻烦,说实话,我也讲不清。我的意思是,读书的后生要是多了,他们以后出去上洋学堂的机会就多,说不定还能出几个做官的人才。虽说而今不兴考秀才了,但洋学堂总要考个什么名堂吧。要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新‘秀才’,他们就会帮我们把世道看得更清楚;要是有了自己的人做官,他们就会为我们主事。总而言之,我就认一个理,一两千个后生子,有种田的,有开铺头的,有做‘秀才’的,有在衙门公干的,黄歇就一定会比现在兴旺,我们万家人的日子肯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们说是不是嘛。” 听罢族长的这番话,尊长们一时陷入沉思。虽然心里认同他说的道道,尤其是为他替后生们的将来操心所打动,但他们还是不吭声。大家面面相觑。 又是老族长打破了沉默,他提议说,办私塾确实不是个小事,我看这样,让我们先回家好好琢磨琢磨,过两天再议吧。 十四位尊长齐声说“好”,便散了。 当天下午,新族长要办私塾的事就在街上传开。在黄歇的三大传统新闻中心——茶馆、剃头铺和交易行,男人们纷纷谈论着这事,说得唾沫星飞溅。 “几千年来都是以种田为本,‘狂风吹不倒犁尾巴’,读书能当饭吃?” “黄歇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族长做了四件事就得意忘形了,是不是他自己想读书了?” “他都四十好几了,读个鬼书。是为他的孙伢儿办的吧?” “有没有人敢跟我打赌?我保证上私塾的不出五个人,开不了几天就关门。要是黄歇出了‘秀才’,我把脑壳剁下来!” “祠堂真是没事干了,糟蹋银子啊!” …… 只有一个人显得特别兴奋。 是的,正是希伯。 一听说祠堂要办私塾,他即刻跑到田里找他父亲。 父亲正在耕田。他站在田埂上喊道,“爹爹,我要读私塾。” “叭”,父亲扬起鞭子在牛背上空地猛地一抽,说:“开玩笑,你以为你才五、六岁啊,都十一岁了,读个屁书。少跟我人来疯。” “我是真的想读了,不跟您打诳。”希伯急得在田埂上直跺脚。读书,是他三年前在寡妇被沉湖的地方立的志向,并非他不想上学,而是李氏祠堂荒芜后便没私塾上了。 父亲停下来,凝视着儿子,想到他这些年在家里读读写写的,确实像个要上学的样子,便说:“好吧,这几个钱我还出得起。儿啊,我晓得要开私塾了,只是怕你读不了几天。” “您放心,我说到做到,保险读下去!”接着他张了张嘴,正想说“不读书我怎么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但话到嘴边,还是咽回了肚里。等读好了私塾再要父亲支持我到外地上学,他早就想好了离开黄歇的主意。 到了第三天,十五位尊长再次被请到祠堂议事厅。 新族长还没开口,老族长就说话了。“作仁啊,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办私塾的事。你前天说的话让我开了脑洞,一两千个后生的前程还真是我们要放在心上的事。他们成人后哪怕不出去干大事,只要个个能认字写字,我看就会比我们强百倍。”他把脸转向其他尊长,“伙计们,作仁想问题确乎比我们深远啊!我赞同办私塾。” 老族长的态度犹如磁石,有十一位尊长被吸住了,他们纷纷表示没意见。只有三位尊长不言不语,大家都明白,这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 作仁族长站起来,双手打拱,连连给他们作揖。“在坐的各位,功德千秋啊!我万作仁代表后生们感激你们!” 接着他说起办学的具体想法。“我匡算了一下,办私塾花不了几多钱,要紧的开支只有两项,一是先生的报酬,一是买书本。学费我建议暂时不收。要是收成好,六十多亩公田的收益是蛮实在的。我想,先由祠堂或是我个人向大家借一点钱,明年用公田的收益偿还,以后就完全靠公田收益了。私塾的位置也不愁,就开在祠堂。上次各位都看见了,中庭摆的桌椅板凳,坐学生完全够用;隔出来的那间小房是供先生住的,先生的吃喝照以前李氏祠堂的法子做,由万家族人各家各户轮流供养伺候。各位觉得怎么样?” “可以的。”老族长等人点头赞同。 “私塾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黄歇私塾。”族长显得非常兴奋。 有人问为何不叫万氏私塾? 族长回答道:“楚国大人物黄歇不是在我们这里住过吗?他是读书人最好的榜样,用他的名字叫私塾,读书的后生们会更加上进,私塾在外面也叫得响。再说,我们这里也叫黄歇,叫黄歇私塾是不是一举两得嘛。” “好!”十五位尊长异口同声。 万氏祠堂办黄歇私塾的事,就这样成了。 次日起,作仁族长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挨家挨户动员街上满五岁的男伢上私塾。跑了两三天下来,只有二十八户的家长答应了他。人数虽然不多,毕竟超过了李氏私塾四五百年的学生总数,族长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宽慰。 第二件是请私塾先生。族长首先登门的,是读过三个月私塾的族人家,诚恳地请他出来当先生。哪知那位老先生连连摇头又摆手,“我哪有资格教书啊,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于是,族长只好择了个吉日,一大早赶到八里外他妻子的娘家,请来一位远亲做塾师。那人年届不惑,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三次赴考,屡未中第,郁郁寡欢地呆在家里。不过,教教《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和写毛笔字,他还兑付得过去。 三月下旬的一个吉日,黄歇私塾开学了。学生拢共十三个,另外答应过族长的十五户,以种种由头没把孩子送来。学生中年岁最大的是希伯,足十一岁。他一直记得那天的情形,在我考上大学的喜宴上,还眉飞色舞地跟我絮叨过。 私塾开学之日,是个晴天,太阳很暖人。祠堂门前吊起两个大红灯笼,石狮子的颈项上系的是红绸布,看热闹的人黑压压的。迎接先生进祠堂的时候,锣鼓齐鸣,鞭炮炸得惊天动地,其盛况堪比过端阳节。作仁族长还讲了话的,现在叫致辞。大意是,我们黄歇闭塞了千把年,万家人的祖祖辈辈只晓得种田、下湖打鱼和开小铺头,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脱钩,人家不晓得我们,我们也不晓得人家。黄歇私塾是万家办的第一所学堂,为的是让街上的后生们有书读。读好了书,后生们将来就有锦绣前程,就会把黄歇和外面的世界勾兑起来,黄歇人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不要看而今学生不多,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不管我看不看的到,我都指望后生们当中出几个有学问和当官的人才…… 希伯说,作仁族长跟我的心是相通的,虽说我跟他从来没走近过。他是黄歇人中最有眼光和头脑的人,没有他力主开私学,我肯定就接过了我父亲的犁尾巴,不可能有后来到南京上公学堂、见大世面的经历。作仁族长是个几难得的仁义之人啊!可惜他后来被冤杀掉了……唉,他死之前,黄歇就陷进乱世,祠堂毁于一炬,私塾从此消亡。真正是水深火热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ly/9839.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我局获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 下一篇文章: 文壮伟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