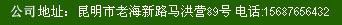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提高江南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南宁市江南区委统战部于年10月29日(星期四)上午开展走进“中国平话文化之乡”同心采风活动,组织多名擅长写作,书画,摄影的文艺者到江南区江西镇同新村木村坡进行采风创作。南宁市作家协会共有15名作家参加。 同心采风活动合影 木村坡地处江西镇同新村,距南宁市区13公里。于年,木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整个村子旧村宅保存完好,村里共有11个古墙石闸门、8条石巷,除此以外,木村百年以上的古树有30多棵,打造的“古树园”主题公园,更是早已于年纳入南宁市人民政府“十一五”规划的11个城区标志性景点公园之一。整个村子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基础好。 村口古树 下车后,作家们很快便被村落门口的古树所吸引,据介绍,那是全球罕见的见血封喉树,此树的树浆有剧毒,被称为“世界最毒的树”,现在这种树存世已经屈指可数,而在木村里最年长的一棵已足足有多年,树高30-40米,分为三杈,每一杈要三个成人围着才能抱住。参观完古树,进村后,依然到处可以看到榕树、樟树、小溪池塘。有作家称古村落流水潺潺,鸟鸣啁啾,古树更是难得一见,有山有水,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同行作家与村民交流合影 一行人还参观了闻名方圆百里的“金石庙”,随后到村背参观了面积高达亩的自然林区。在整个采风过程中,作家们热情高涨,纷纷拿出手机,捕捉美景,感受木村坡古村落的魅力,并且还深入村民中去,与村民交流,有说有笑,感受他们鲜活的生活,为写作搜集素材。 南宁市作协副主席韦毓泉、侯建军等人参与了这次采风活动,他们表示作家不仅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更要有一支能够写好写活身边美丽景色的笔杆,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南宁美之所在,为家乡的宣传贡献一份力量。 同行画家写生 作家参观古树、石头巷附:活动当天部分作家采风作品陈坤浩,95年生。广东揭阳人,现居南宁,曾参加第十二届星星诗刊大学诗歌夏令营。 如此之久了,你的站立 ——记江西镇木村古树我们来到木村的时候,你正迎着小雨在十月的末尾,包裹于潮湿之中古树是你的语言湿漉漉的时间道出三百年他们念出你的名字,与死亡相关领事说你是一种罕见的树种存世的已经屈指可数但我很难想象其他的你会以何种孤独的形态出现在游客面前当然我也无法如同行的画家一样将你的细节捕捉在这朦胧的雨雾中只能将手轻轻地放在你身上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如此之久了,你的站立或许早已消除了一切声响。什么都听不见你的内部,血液在流,缓慢不惊世那是世代人体内所流的我明白,每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少年心里都应该有这么一棵树与外界无关,没有名字没有种类,当想起的时候雨就浸透了你的身体好比,此时此刻 秋枫,原名谭漓,女,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绿城玫瑰”作家群成员。喜散文、诗歌、杂文以及评论。 木村半日“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秋天来的时候,又去了木村。与木村的结缘,不是竹院,也不是高僧,而是老罗和见血封喉树。将近二十年前与老罗同事,老罗当时在文明办当副主任,我则分管新闻和媒体。老罗常跑县区和农村,而我一直属于象牙塔里的一介书生,又来自北方,许多方言听不懂。所以与老罗同事期间在单位里极少见面。但每逢见面,老罗都极热情,他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腰杆笔直,声如洪钟,仿佛这世上就没什么事能难得倒他。一个周末,老罗跟我说他的老家在南宁市郊的木村,邀我去看看。我问:远不远?他答:不远。我问:路好不好走?他答:不险。然后他笑眯眯地劝我:“你一定要去木村!那里有见血封喉树!”“什么?!见血封喉?!武打小说里的那个见血封喉吗?真的有树?”不能不说,老罗抓住了我的好奇心。于是,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同事一起跟着老罗去了木村。时光荏苒,路是怎样的弯弯曲曲,我已不大记得到底是怎样去到了木村。总之,当时没有导航,也不是我开的车,就稀里糊涂地到了,感觉上是南宁市区的西南方向。一下车,老罗就带着我们去看见血封喉树,我只记得有几棵大树参天挺拔,树干粗到一干人都无法合抱,树干笔直,大约老罗打小就是看着这挺拔的大树长大的,所以腰杆笔直。树干十几米高之上,枝叶茂密,遮天蔽日,一种沧桑和苍翠之感油然而生,且近二十年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不曾忘记。上周四早上,刚刚好有半日无会,跟随美协、摄协、作协的艺术家们乘上大巴到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的同新平话村采风。兜兜转转,车过了白沙大道,一路向西……路边出现了“杨美古镇”的路标时,车向左转去了“同新村”。这条路仅仅是村级的水泥路,五十座的大巴会车时还真是考验司机的技术和职业操守。大巴车的车窗擦弯了路边的柔软的榕树枝,停车下来,“木村坡”三个白色的大字立在路旁,在绿树中间赫然。哈!老罗也在!老罗已经先头开着自家车到达。一晃,十几年没见到老罗了,他已退休十年,似乎与我们同事时没什么两样。这次,老罗又成了主角,向画家、书法家、摄影家、作家、媒体记者介绍着木村悠久的历史和“美之所在”:木村依山近水,明清古民居集中,树木繁茂,珍稀古树经专家鉴定最老有年……木村人讲平话。村头戏台上,打对面,在武警某某中队捐赠的条椅上坐着一排中老年男性和女性村民,男左女右,他们现编现唱,用平话对着“山歌”。平话,是古汉语在广西地区得以保留和演变的一种汉语方言,世代说平话的,一定是汉族。相传,宋代狄青率部平定广南西路起兵反宋的农智高,部队大多以“山东”人为主,彼时“山东”指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平乱之后,一部分士兵留守戍边,其后裔在此生息繁衍,发展到了今天,与当地的壮族同胞相融合,居住在周边的壮族村民也有会说平话的了。他们唱的什么,我不懂,但调式婉转激越,我努力循着,想与今天的河南豫剧、山东大鼓、山西梆子一类找找共同点,走在村里的石巷中,顺风侧耳,反倒觉得有些像邕剧了。说起木村的石巷,老罗这次费了许多的“口舌”。第一次来木村,老罗牢牢抓住我要看见血封喉树的好奇心,只带我看树,见血封喉树和大片的松林。因为是时间有限,没能进村。这次跟紧了老罗,过了头道石门和二道石门,大家都被门拱上足有一米半厚度的“仙人掌”类植物震惊了,我们看着像火龙果的三楞枝条,老罗说这是“蕃鬼莲”,这石拱门就是古闸门,以前有木门和木栅栏,闸门开在2米多高的石墙上,是类似于“城墙”的围村防御墙,用石块垒成。石墙和石闸门上种满刺人的“蕃鬼莲”,是村民防御外来入侵者的屏障。我们进的头道闸叫大闸门,二道闸在其内部筑起二道防线。两道闸门的左侧是外墙,比较厚。右侧是内墙,比较薄,是几家姓氏的分界墙。内外墙之间是石块铺就的石巷,不大宽,有一两米,就着山势,自然弯曲。这是从东入村的主要通道。进了二道闸,才能进到村宅里的依次罗家、廖家和邓家。老罗如数家珍,对木村的石头有着太多的充满了亲情的记忆。天上正飘着秋雨,不规则的赭石色的“三面光”石块铺就的石头路面光滑如洗,岁月早已磨平磨光了这些石头。老罗想起了有一年的农历七月十四,是本地传统的“鬼节”,即中元节,要用“碎菜”(鸭肉、粉丝等)在大屋(宗祠)的中堂供奉祖先,然后才担到百米开外的下屋的厨房,家人用餐过节。正好赶上暴雨,老罗的父亲出了中堂的门在石头台阶上一滑就摔倒了,装在篮子里的“碎菜”撒在石头上被水流冲走。老罗的父亲急中生智,赶忙用篮筐在巷口截住菜肴,再回锅热一下,如新菜一样干干净净,是全家人的美味佳肴。进了二道石闸门就是罗家的门楼了,青砖砌成,基脚是石头的,有一米多高,用石头砌成了台阶,连着一段石墙,石头都是赭石色的。进了罗家的门,依然是石巷,老罗带我们到了大屋,三间青砖瓦房,屋檐下有檐廊,一米来宽,两三个台阶通往天井。中间是正厅,左右对称是居室。正厅也叫中堂。中堂的后三分之一处是一面木质的壁巴,有张四方的八仙桌,两边各一把椅子,靠在壁巴前。壁巴上方有木阁楼,需要架梯子才能上去。以八仙桌为正中,通常在壁巴上都贴着中堂和对联。这就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也是迎客的接待场所,亦是家族长者训诫子孙的厅堂。壁巴的右边有一个门,通向房屋的后门和右侧的居室,老罗说这间居室是他的婚房。老罗家的老宅虽说不是明清时代的古屋,法式却如出一辙。这是南宁郊区普遍式样的“广府民居”,所谓“三间两廊”式民居,但没有镬耳山墙,取而代之的是飞檐屋脊。屋脊的正中央通常有一个铜钱状或者宝塔型等装饰。三间青瓦房,中间为厅堂,左右对称的居室。“两廊”一般为厨房和门房,与三间瓦房的檐廊相通,能够遮阳避雨。不过,木村的“两廊”被院墙取代,只有一个小的门楼。通常,院门开在右边的院墙,进门有天井,天井有下水的设施,用水泥浇筑的地漏上长满了青苔。两三个台阶上到檐廊,门口有木质的门槛。进门就是正厅了。老罗当年的婚房已经空空如也,老宅已经无人居住。出了老罗家的后门,紧挨着的是另一家的檐廊,两条檐廊中间是一条小过道,右侧开门,可以通向村里的石巷。出了罗家便是廖家,廖家的石巷很长,里面别有洞天。挨着廖家的门楼,是邓家。邓家的古屋看来有些历史。大屋(宗祠)的门簪上左右刻有乾坤八卦图案。乾卦在左,坤卦在右。宗祠檐廊上,大门两侧有两根圆木柱,柱脚的石雕非常精美。下了宗祠的檐廊,过了天井,是三间小一点的瓦房,门簪上刻的是坎卦和离卦的图案。门楼对着的院墙左侧是空间很小的二层碉楼,上有两条竖的枪眼。关于门簪上的八卦图案,木村清代留下的古民居都有。有的就是门簪的方形,有的则雕刻成菱形莲花状的,线条精美,凹凸有致。按照民间对八卦的理解,乾坤乃天地,以天地为“父母”,坎离等其他六卦为“六子”,说明世界的生成根源,又以乾(天)与坤(地)、震(雷)与巽(风)、坎(水)与离(火)、艮(山)与兑(泽)之间的相互对立和刚柔互易,表示事物的相互转化和发展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哲学思想。同时,按照民间对八卦的理解,乾、坤、坎、离四个卦象处于正位,又相生相克。以此,我猜测,这下房住着的,当是儿子。又或者,是厨房。只不过这些民居都没人住了,我一时无法去核实。木村罗、廖、邓等几大家族开枝散叶,老院子住不下了,纷纷到村外建了新楼。木村自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政府投入了八九百万修缮古民居和兴建村戏台,修筑进村硬化路面等,使传统村落的文化能够得到保护和传承。这个结果,与老罗二十多年来不懈努力分不开。出了邓家的宗祠,我还是意犹未尽地去看村头戏台旁的那两棵上百年的见血封喉树。画家和书法家们早已拿出笔墨纸砚,描摹着古村古屋古树,摄影家镜头对着古榕下的老人和孩子,他们闲坐着听台上的对歌……见血封喉树,粗糙的灰色树皮上布满时光的褶皱和疤痕,仰头向上,椭圆倒卵形的叶子在秋风秋雨中摇曳,沧桑中透着神秘。旁边的古香樟已有三四百年的树龄,树干长满了青苔,树叶依然细腻苍翠。古榕硕大的树冠和众多的气根扎在磐石的缝隙中,荫护着祖祖辈辈的木村百姓。这些三四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历尽人间沧桑与烟火,依然挺拔向上,茂密的枝叶在秋风秋雨里婆娑着诉说,真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年11月1日于邕江北岸…… —END— 红豆杂志 张开文学的翅膀, 《红豆》连接你我, 连接社会与个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fz/9346.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文明聚焦江西9地入围国家级重磅名单,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