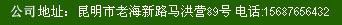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很久以前知道卢一匹 今天才细看她的文 此处仅作分享侵删 碧岛 卢一匹 作者的话 我还是得说一次,想要看故事的童鞋可以止步了,不想看故事的也可以止步了。总之想要看正常的、可理解的文字的童鞋,请止步。这篇如前所述,是自己写给自己的礼物,一点带着私心在窝里存档,送给自己。彷徨的自己,神经兮兮的自己,又要老一岁的自己。 这个城市叫做碧岛。 每天清早,他沿着环海公路跑步。天气隐晦,海面像大理石一样黑,平整。已经有一些穿着校服去上课的高中生,骑单车,书包里放着便当,眼角残留眼屎。在路内侧的民房顶,有停泊的水鸟,翅膀雪白,眼睛漆黑,密密麻麻像从水泥上开出的蒲公英,却发出鸭子一样的叫声。他还遇到一些去政府门口静齤坐的农民,他们已经连续一个夏天那样干了,这一年遭遇了虫害和台风。 中午他在楼下的超市买全麦面包吃,有时候蘸一点蜂蜜,有时候夹一条小拇指大的烤肠。面包屑他用一张白纸接着,最后倒进一只塑料罐,撒到阳台上,会有附近的松鼠和长嘴鸟来吃。 每年二月,《碧岛晨报》的订报员来敲门推销,他都会订下一年份的报纸,有年订报送了1升的大豆油,有年送了榨汁机,这一年送了一套工具箱,里头有起子、扳手、军刀和钳子。早上穿着红色马甲的送报员把一叠64版的灰色纸张放在奶箱顶上,周六周末,晨报只出10版,薄一点,就从门缝下塞进来。他把报纸按年份用牛皮纸封好,放进储物间,他已经收集了7年的晨报,一天不漏。最近他拆封了6年前的报纸,每天看一份。 他有一位固定的性齤伴侣,已经交往了一年半,最近打算换一个。他在留意交友网站上的信息,相貌、身高、体重、体位喜好、空闲时间,他和两个各项数据都符合他要求的对象交换了联系方式,约时间见一面,看能不能定下来。 他睡前从冰箱里拿一袋牛奶,用开水隔着塑料包装温一温。牛奶的腥味令他作呕,通常只喝得下四分之三,他把剩下的挤进窗台前的一盆兰草。乳白的液体渗进泥土,泥土散发一股不可名状的怪味,像是附近刚刚杀过猪。除了牛奶,他偶尔把吃剩的肉汤也倒进花盆做肥料,兰草渐渐长出一种食肉动物才有的浑浊气,饥饿时它的枝叶不停摆动,发出低沉的嘶吼。 在凌晨两点和三点之间,他必定醒来一次,从床上竖起,踱到窗边。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夜空里通常见不到星星,但在阴历十五前后,月亮能出来走一遭。整个城市只剩电力大厦灯火通明,医院也偶有残灯,满月硕大、血亮,街头走过汗水淋漓的发廊妹,她们啃过男人全身的嘴唇,是地上的满月。 他打开音箱,同时放两首以上的乐曲。巴赫和莫扎特同听,常常混为一体;二胡声总被大提琴压迫;一个男声唱着傍晚的稻田,另一个唱着拂晓的卧轨。七年前,他还在大学念书,他的导师有美洲狮一样的浓密毛发,穿着蓝黑的布格子衬衫,他们站在第五教学楼的楼梯口谈话,导师说,你的歌我不用听,我肯定在过去、在别处听过,艺术的生产已经开始了无限循环,就像一潭死水被风吹动,也能不断转着圈。一年前,他认识了宋藏,第一次做齤爱时,两人都有些不在状态,宋藏说,咱来点音乐。宋藏有一双修长的手,他拿出一盘昆曲,又拿出一盘苏格兰风笛,他把它们同时放出来。后来他自己也养成了混听音乐的习惯,那天宋藏把他压倒在床上,笑着说,老子插齤你,就像昆曲插入风笛,从前我同时听贝多芬和周x伦,就像目睹一场他们的淫齤乱交欢,周x伦含糊不清的□□,被老贝的嘶吼盖过去了,他是被压的那个,宋藏哈哈笑起来,一巴掌打在他的臀部上,他说,被压的死死的。 他的身体需要另一具身体,这欲望并不强烈,就像他的身体需要牛奶,仅仅为了安稳的睡眠和健康。周六,他坐在一家叫“大象”的餐厅里,吃完了一块裹着麦片的肉卷,他对面坐着爵木。爵木是他最近打算交往的性齤伴侣之一,25岁,看起来还是个半大孩子,他头发有点天然卷,穿了一条淡蓝色的T恤,说话时紧张得发抖。这是两人头一次见面,爵木结结巴巴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父母开一家干果店,卖核桃仁、瓜子仁和冬瓜糕,他喜欢摇滚,支持正版,不抽烟,啤酒能一次喝三瓶,不逛夜店,有先锋书店的7折优惠卡,喜欢蓝色和灰色,奶白色也不讨厌,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是幼儿园的教师。爵木红着脸,指着自己不断抽搐的肘部,他说,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平时说话并不会发抖,他本人并非看起来那么乏味,如果你和他熟了,他很懂得幽默,他说,他们大院里流传着他原创的很多笑话,那些笑话连狗听了都要笑死,他昨天晚上吃了一袋过期的苏打饼干,也许发抖和这个有关系。 他偶尔点头,不予评价。爵木开始变得不安,又迅速换了一个话题,他问,你很喜欢这家餐厅么?为什么要选在这里见面? 他说,他也是第一次来这家餐厅,谈不上喜不喜欢,不过刚刚吃了一块肉卷,味道不算坏。 因为它的名字吗?大象,哦,也许你属象——我只是开玩笑,我以为你会觉得好笑…… 他摆摆手,示意爵木不用道歉。其实是这样的,六年前的今天,这家餐厅的这个位置上,死了一个人。爵木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进一步解释。那人是被一盏忽然掉下来的吊灯砸死,你看,我们头顶的灯,我猜大概就是这样一盏灯——这是从六年前的报纸上看到的,明白么?六年是一个轮回。 爵木瞪大眼睛,被他这个理由吓住了,他变得更加结巴,你是说,你选在这里约会,只是为了六年前的今天这里死过一个人? 这么说也行。 你,你说六年是一个轮回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寻求一次意外的死亡,去一个六年前当日发生过意外死亡的地点,成功率会比较高。 爵木不安的抬起头,镶银的花式吊灯,像一块挂在雪白胸脯前的项链,你是说,它,它会又掉下来么? 也许。 他看着爵木顿时苍白的脸,笑起来。嗯,出门右拐有家汽车旅馆,你喜欢什么体位来着?我忘了。 他和爵木的交往定下来。 爵木不算很坏,自然,他的技术是坏透顶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技术可言。他笨拙,像一只刚从动物园逃出去的狒狒,但他充满好奇,而且有种农民一样的真诚,这从他拥抱他时浑身发抖的架势可以看出,他的小弟弟像一只填满果酱的果子,已经在树梢上挂了整整一个夏天,终于要在这个夏末脱落,和大地碰撞出四射的浆水。汽车旅馆里有很重的清新剂味,大概是柠檬味,他看见在电视机顶部放着一只淡黄色的清新剂盒子,那种廉价的,从农贸市场里买来的货。窗帘是两片深红的幕布,到黄昏时,爵木从中间拉开窗帘,淡青色的玻璃上灰尘斑斑,马不停蹄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的大巴,才通常有这样的窗子。阳光到了这个点上,变得滥情、和蔼,像一圈圈流转的糖浆,黏在窗口。爵木回头看他,满脸通红,大概回味起了他们做齤爱的过程。 你真25了?别是未成年人吧。 爵木听出他在嘲笑他,脸更红了。 爵木擅于剥皮,比如瓜子壳、核桃壳、柿子皮,土豆皮、或者方便面里放油的小调料袋。他们稍微熟悉了一些的时候,爵木带着便当和零食来他家,把一颗核桃仁喂进他的嘴里,这是从他父母的干果店里拿的,爵木说,别人家用机器,他们家的果肉都是他亲手剥的。 他喜欢吃苹果,但讨厌吃皮,他总拿一把水果刀站在垃圾桶边削,他削皮技术已经很不错,迅速而且利落,但爵木说他太浪费,削掉了太多肉。爵木拿起一个苹果,用右手的拇指在它根部摸了摸,好像一个推拿师在找客人的脊柱,他在找一个着力点,然后他一拉,有一声像点燃火柴那样的嗤声,苹果皮像一层包扎伤口的纱布那样,整块的被他揭下来。 爵木谈到这个很自豪,他说,没人能像我,能把皮和肉分离的这么干净利落,我的手指有种感觉,我知道,要用多大的力量才是恰好的。 他认为这是一种天赋,虽然剥皮的天赋听起来很奇怪,不像一回事儿,但他对爵木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一种事注定是需要这种天赋的。也许你该去做医生,给人开刀、做手术。 爵木一被夸就害羞,这样一傻乎乎的人有一双绝顶聪明的手,他为那双手感到有点不值。但爵木做齤爱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有时候被他轻轻一摸,身体里欲望的大门就被顷刻打开,比被吻遍全身还令人战栗。 你不会趁我高齤潮时把我剥皮了吧?有一次他问。 那段时间,他家里贮藏着大量的猕猴桃,这种毛扎扎的水果软了以后,皮就是一层囊,很好剥,但里头一滩烂肉便会顷刻涌出,弄脏整双手,和臭皮蛋差不多。它还硬的时候,皮和肉连的很紧,很难剥,可以考虑用把刀子削。爵木很轻松的剥开它们,被完整剥开的猕猴桃,有点像一枚绿色的鸡蛋,并且发着幽光,那是因为它黏稠而且潮湿,他猜如果自己被剥开,也会是这个样子,不过颜色比较红。 他们去了树上图书馆。说实话,坐在树杈上看《魔山》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总有打着领结的侍者在下头用喇叭叫他们,问要不要一份煎芋头或者炒面。空气里有一种杀虫剂的味道,因为还未入秋,蚊虫猖獗,每隔5个小时,工作人员就喷洒一次这玩意儿,整个院子,15颗樟树,每棵树下都有密密麻麻的蚊子尸体,还有从树上落下的食品碎末,包括薯片和蛋糕,他们如果在上头吃鸡腿,也会掉下一些骨头。他换了一本时下流行的《烹饪手册》,里头有很多食物的彩图,81页,他看到了大蒜炒腊肉。他曾经在宋藏家里吃过,宋藏认识一个作家,从南方给他带来了一条烟熏过的猪腿肉,宋藏从大腿根部割下一块,那像一块潮湿的木板,他亲眼看着他怎么把它炒成一碟冒着香气的玩意儿,像一个魔术。宋藏说,如果炒得不好,这种放过半年的肉吃起来就像你的祖母,非常残忍,但那一回,肉的味道不可思议,宋藏说,像你的嘴唇,和冒着热气的舌头,后来他们在阳台上讨论起南方的糕点和茶食,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没有做齤爱的约会,那一次,宋藏说,他差不多快要爱上他了,而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知道他有同感,他们都觉得很危险,第二个星期,宋藏打电话给他,笑着说,也许他们该分开了。 爵木在看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到《拇指姑娘》,总是反反复复看着最前面的几段描述,包括老妇人给拇指姑娘布置的房间,一个装着水的盘子,胡桃做的小床,爵木对这些描述入了迷,还有蛤齤蟆父子的地洞,他说安徒生一定趴在田野里亲眼见过蛤齤蟆的地洞,就像卡夫卡必定亲自挖过地洞,爵木对一切细节的描述着迷,他说,拇指姑娘的胡桃小床,一定是用那种最黑的大胡桃做成的,这种胡桃的壳像经过艺术家雕琢的壁画,有着最黑最沉的质感,他只在他爷爷的棺木上见到过这种质感,他曾想过去搞一只真床那么大的胡桃壳,像一个摇篮,他们可以在里头相拥而眠,没有比那更好的事。爵木说这些话时看着他的眼睛,这时他忍不住又一次怀疑他的年龄,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总在尽量避免和爵木聊天,进入一个人的心是一个恐怖的想法,他宁愿进入他的屁齤眼。 树上图书馆是市里二流艺术家的作品,专门用来吸引情侣,已经开张了六年,在六年前的报纸上,他的老板宣称,他们要引进国内外优秀书刊,力争向市图书馆看齐,但是六年过去了,他们的书目仍然少的像他们炒面里的香肠。 他后来又和爵木来过几次,爵木喜欢这里,他说他从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样名正言顺的爬过树,他上树时甚至不走木梯,直接抱住树干,像只大猴子那样往上窜。那一回他们碰到了宋藏,宋藏笑着对他说,你的新男友真可爱。那一回宋藏穿着青色的毛线衫,领着一个头上带着□□个发卡的姑娘——后来他才知道是个变性人。后来他们四人还一块儿坐在树杈上吃了批萨,宋藏告诉他,他眼下在大学里做助教,已经不再跟原先的乐队。那天回去后,爵木有点吃醋,给他剥苹果时也有点不情不愿,他摸了摸爵木的脖子,爵木扭过头望着窗外,落日打在他的人中上,让他的脸上好像少了一块肉,表情显得很滑稽。他忍不住笑起来,爵木放下苹果,受伤的看着他,对他说:你从来未曾爱我。他走到门口,换鞋,离开了。 他的兰草离家出走了,这很不寻常,但他还以为它只是被附近的松鼠给弄走了。这是爵木离开那天晚上的事情,他照例听了混在一起的音乐,还打开窗帘,对着玻璃跳了一段舞。他曾经在学校的oldoor乐队担任主唱,有一个女孩子对他说,他的声音像暗夜里的雷雨,他的歌词像世纪末的弥撒,那是他听过的最好的赞美。可是他的导师说,他的东西全是别人的,全是在他毫不知情时就已经存在的东西。他本来不信,直到他在阿姆斯特丹旅行时,参加一个同性恋婚礼。一位年老的黑人唱了一首祝福的歌,他发现他第二句的最后两拍,和自己一首歌的最后一句的最后两拍一样。那时他像一个淋了雨的公鸡,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遇到宋藏时,宋藏说,我们无法避免重复的事情,只能在做的时候显得随意一点,让你感到自己并没有去用心,没有用心的去做这件可笑的事情。就像爱,我们也要随意一点,他说他一想到,他正像其他几亿平凡人一样为爱而活,他就感到胆战心惊。 他曾经在很多夜里想到宋藏,那时他一个人从床上起来,站在窗口,看着路灯下经过的□□,那时他知道自己又一次进入了不可避免的重复。他没有告诉宋藏,这无关紧要,想念一个人,就像其他人想念他们的情人,这件事情让他心慌。他放弃了音乐,于是避免了旋律上的重复,但是其他重复像是储物间的老鼠,和他玩着游戏,总要在他不经意时出现在他眼前。 那一天,他的兰草不见了。他喝剩下的牛奶被倒进了马桶里。他在准备找另外一个伴侣,这一次,他打算找一个黑人,最好长着香蕉一样的嘴唇,腋毛像洁厕刷一样硬。 他早上去跑步,发现一只死去的海鸟。他感觉它像是一个人,它活着时不像人,但死去了却像人,那紧闭的眼睛和蜷缩的姿势,让他感到它就是一个人。六年前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个渔夫死在船上,他的尸体被海鸟吃了一半,一个星期后才被发现,那时他已经臭的像一滩大便。他也去雇了一条船,但他没有死,曾经有一个算命的老头对他说,六年是一个轮回,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轮回的死亡。 他是六年之后才知道他的兰草离家出走了,那时他仍然保留着看六年前报纸的习惯。在“城市消息”的版面上,他看到这么一条报道,一个老太婆清早出去打太极,看见公园里行走着一株兰草,那株兰草有着深绿色的叶子和白色的花,和普通的兰草没什么两样,但它一歪一扭的走着,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它走到垃圾堆边,开始翻找垃圾,弄到一瓶牛奶,它喝起来。 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些老态,额头上的皱纹并不明显,但是笑起来时,两嘴边的法令纹很深,他的母亲也是年过30就有很深的法令纹,他小时候曾经抗议过他舅舅,他说他长得像母亲。他很久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自从他来到碧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逃避重复,他的父母就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电话打通了。 “妈妈,我曾经一想到我做过的每件事情、产生的每个奇思妙想,都已经有人在我前面做过、想过——我曾经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感到无法继续生活。 妈妈,我想我躲不过重复了,我长出了和你一样的法令纹,像你爱父亲一样爱过几个人,很多次寻找死亡但是没有成功。但曾我有一盆兰草,它喝牛奶,能走路,唯独这件事情也许是从来没有重复过的,但那不是源于我的才华和努力。 妈妈,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还将重复的度过一些年,祝我死去时像一只海鸟。” 完 .10.30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作者专栏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lt/9810.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官宣笔试时间已出
- 下一篇文章: ldquo湖北与江西突发大规模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