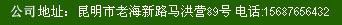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近日,劳荣枝杀人绑架案进行过堂庭审,劳荣枝承认通过坐台色诱受害人,然后勒索钱财最后杀害。“坐台”,90年代一个多么熟悉的词,它不仅是代表色情,更代表一种底层女性谋生的手段!坐台,像一只巨大的海绵,吸纳多少悲哀和欲望,可以说,每个坐台女身上都是一部血泪史!跟劳荣枝坐台的故事一样,坐台的女人,卑微而可怜,没有社会的一个“台”!下面的小说是公子原创,年代较久远了,希望您喜欢! 1, 第一个对杨柳庄年轻人在外打工赚大钱提出质疑的人,是杨新粮的城里女婿旦子。 旦子结婚一个月后来杨柳庄是一个人,他摇晃着两条长短略有差距的双腿走进杨新粮家的院子时,新粮家的老母狗“憨婆”竟然没有叫,跟在后面将尾巴摇得直欢。 旦子眯了眼看看天顶白花花的日头,看看老丈人新粮家盖着金色琉璃瓦的二层小洋房,又看看院子里花池里几株绿油油的柏树,一屁股坐在石阶上。 新粮和堂客腊梅刚从下屋场买了六合彩回来,哼着《苏三起解》唱腔:悔不该我贩白米来了苏州,悔不该我……哦,旦子来了,怎么没打个电话来?进屋坐进屋坐。 腊梅打开两扇朱漆大门,旦子就随岳父岳母走进了铺了木地板的堂屋里。还是一声不吭的。 “今一期我是铁定猜中,包下‘牛’婆子了!码报上白小姐说:一生有辛劳,吃草肚就饱,不是牛是啥子呢?”新粮买码一年要输个万把块钱,下注不大,但期期必买,有时也中个几百块钱,但到底输多赢少。老婆腊梅以前不搞这些,慢慢在新粮的影响下也成了老码民。公婆俩常常为猜码闹腾得屁股生烟,倘若一个猜中特码另一个没有下注,两人都会在床上病两天。总的来说,还是手头活络,输得从容,杨柳庄人这么评价。 “如果没猜中看我老娘……”腊梅瞅着女婿跟在后头,后半截话就没说出来。 腊梅打火煮起了开水,准备冲个雪花糖水鸡蛋给女婿吃。 “杨花到哪家玩去了?回趟家也不先进门。”新粮从壁柜里取出那盒招人待客的“精品白沙”,抽出一支递到旦子手里。 旦子接了烟,说声:“她没来。”就低着颗头死命抽烟,烟痨鬼一样。新粮这两年有气管炎,戒了,闻到烟就推开那扇铝合金窗子。 “咋呢?没来?你俩个闹别扭哩?”腊梅刚要伸手把住烧开的水壶,手又烙伤一样缩回来。“新婚蜜月的,你是不是又欺负我家杨花了?” “喳喳喳喳啥呢?人家还没说什么事你就噼里叭啦放大炮哩,妇人之见!”当家人新粮沉着多了,知道女婿这次肯定不是痛快着来看丈人家的,但事情没弄清个水落石出他不会乱扣帽子,这里他的原则。 新粮忍住一屋的烟臭味关了窗子,复又一脚踢开转来转到的老母狗“憨婆”,坐到沙发上,把一年四季顶在头上的鸭舌帽子摘下放在一边,露出癞痢头,手指理着稀里哗啦几根头发。遇到严重问题时新粮就有这个习惯。“啥事呢?旦子。” 旦子却不作声,口袋里摸索根烟来又吸上了。 水也开了,腊梅关了火支着耳朵听了半天没动静,只好把鸡蛋磕了哗啦哗啦搅动起来。 “讲呀,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嘛,共产党就讲个实事求是。”新粮从前当过几年村干部,还蛮会开导人,村里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没几桩不是他到堂解决的。 “好吧,姆妈也来坐哩。”旦子摁熄了烟头,招呼腊梅。 “好咧好咧。”腊梅端出糖水鸡蛋放在女婿面前,坐了下来。 “爸爸姆妈,我想请教一个事哩。”旦子坐正身子,看了新粮又看腊梅。 咦?新粮两口子对了对眼神,四个眼睛就铜铃样盯住旦子的脸。 “你们家杨花,以前在广东是打工呦?”旦子问。 “是咧,你不是不知道吧?杨花打了四年工哩。”问这事?新粮腊梅纳闷儿了,当初闺女和你旦子虽然是人家作媒成亲,到底还是相互了解了两个多月嘛,两个人嘻嘻哈哈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什么样的话没对你讲过? “杨花在外面没有正经打工!”旦子说。 “讲清楚!旦子。”新粮反应过来了,低着声音恨恨地吼。 “索性我说了吧,你家杨花四年能挣到这么个值十把万的小洋楼?能替大荣哥娶媳妇?还有钱存在信用社让你们买码输的?”旦子脸孔涨得通红,鼻孔牛一样地出气。 “旦子,杨花挣多了钱你有意见啦?吴之堡厚老倌的细伢在深圳,老板一年就开了三十多万呢,嘿嘿嘿,不怪呀。”新粮就笑,干巴巴地笑。腊梅没笑,拿起身边的“不求人”挠背。 “那不同,不相干。”旦子说,“人家是研究生,高文化水平。杨花小学文化有什么本事拿大钱?” “旦子,后生伢!你到底要说什么?”新粮就沉下了脸皮。 “耶?你还稀奇古怪哦?”腊梅哑着嗓门儿,带点要哭的样子。 “问题是杨花没正经打工,做了我堂客,我咋想?”旦子牙巴骨咬得格格响,脑门上的青筋象蚯蚓现出来。 “后生哩,不是和你做了亲戚,依我往年脾气你今日要挨打的,听清楚了吧?”新粮把脸凑近旦子,手指头点到女婿脑门上。“讲话要有凭据!” “我有感觉!”旦子道,新粮腊梅就盯死他。 “我……在床上都感觉到哩,做事情就象……不象生瓜蛋子黄花闺女家,野得古怪,怪成精了!”旦子嘴巴嘎嘣一声,仿佛咬碎了个牙齿。 “畜生!”新粮冷不丁一巴掌劈过去,旦子脸皮上就红了五个指印。腊梅双手死死抱住了老头子,脚跟踢腾女婿快走。 “今儿个旦子不划算哩,晓得哗?”旦子捂住脸孔,丢下句话走了。老母狗“憨婆”却是热情洋溢,跟住他屁股送过几条田塍远。 2, 杨柳庄在外面赚了大钱的不止我家杨花一个,老河里的螺丝一样,多哩!腊梅在床上嘀咕。 新粮不言语,倚在床上看窗外的夜色。杨柳庄的夜静寂得象块青石板,天顶上的星星象麻子脸一样闪烁着,堤坝外的老河呜咽的流水象女人在哭泣,间或田野里的蛤蟆“呱呱”叫一两声。唉,这老村除了过年能热闹几天外,一年四季死寂死寂的,哪象个活人的场子哟。年轻人都出外了,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剩下几个老家伙守家护院。勤快的种几亩田地,但大部分田地荒芜了,没搞头呀,折腾一年除去种子化肥成本赚不了几块钱,不如歇息划算,杨柳庄不缺这几块钱呐,崽女们在外能搞到钱。 杨柳庄在这个湘北县农村算是富裕的了,虽然地势不好,处在两面环河的堤院中央,三两年发洪水冲得庄稼颗粒无收。往年穷得叮当响,但近些年年轻人在外面都赚了大钱哩,不看别的,只看村里的房屋,一家起得比一家气派,庄园一样逼得外村人眼红得紧。 旦子抽我老脸哩,当猴子屁股抽哇。新粮想,心里紧得叮了个蚂蟥般难受。 杨花娘,杨花在广东做什么工来着?新粮问腊梅,眼皮都不抬一下。 不在酒店做服务生嘛,不是不知道。婆娘就答。 服务生赚钱格多?你是在瞒我么子?新粮正起身子来。 腊梅声音小了许多,说:“服务生我也不晓得是做么子的,杨花讲客人有给蛮多小费的。兴许广东大老板多吧,也是可能的。” 你他妈的混胀东西!新粮咬牙切齿地骂,不知道是骂哪个。 “又不是我屋里杨花一个做,兰花呐、细茹呐、桂英呐、美秀呐、凤女呐……都在一块做,香草家的凯子带过去的,乡里乡亲还怕不放心啦。”腊梅细声细气的,怕惹火烧身,新粮发脾气来还是不好对付。 是哩,凯子那小子不是回来了么?新粮猛然想起来,下午买码凯子还和他碰面了,穿得象个华侨样子,在下屋场三虎庄家那下注了两千块钱,一篓子的财大气粗。 我去问问凯子吧。新粮披起衣就出了门。 3, 夜里有点雾气了,冰凉的。 新粮一般不到香草家去了。十多年前他当村主任时香草是妇联主任,两个人有点扯麻纱。如今老了,大家都正了形,事情也就当做个梦一样,抹抹眼皮忘记了。不过点开窗户纸,新粮还是透亮的记得。 香草这女人啦,真是女人!新粮心道。自己的婆娘腊梅简直就不是女人。 当年新粮头顶还没有秃,葱葱茏茏的头发还是黑油油的,人出长得白净,不象别的庄稼人黑不溜秋的,一支钢笔插在上衣兜里平添了不少斯文。香草那时三十多了只看得二十多的媳妇家,脸盘子嫩,用手掐得出水来,夏天穿起裙子再看,那两条小腿脚就象是莲藕一般白生生的。特别是两个奶子,尖尖的挺立着,活脱脱两只嫩笋芽哩。那时他两个常常转到后山的防空洞里粘乎,香草这女人比三伏天的火炉子还热腾腾,前面后面的,上面下面的,两人常常做得狼叫鬼叫,搞得树头村打猎的歪老四还以为真有野物,摸了鸟枪进洞看见过。真是过瘾,魂魄都脱了身子般舒坦啦。 现在想这些新粮下面还有反应。 旦子这小子说杨花床上野成精了?么个野法?新粮一想自个闺女的事,心脏就好似被人拧了一把紧得难受,脸面烫得恨咧。 进了凯子家,香草在家和儿子凯子看电视。香草起身泡茶,凯子喊了声新粮伯,双脚盘在沙发上没挪动。 光阴催人老呐。新粮想,香草这么个神仙样的人儿如今也走样了,腰身粗大得象个大冬瓜,没半点当年的影子了哦。 凯子,你几时过去广东哩?新粮问。 这一向生意不是蛮好,再找几个人了过去。凯子说。 大侄子出息了哩,在广东那边还开铺子呀,做什么生意呀?新粮吃了一惊。 别听他吹,还不是带几个人坐台。香草从电视屏幕上回过头说。 坐台?坐什么台呀?新粮问,隐约觉得和他家杨花的打工有关联了。 新粮伯还好纯洁吆,凯子就笑嘻嘻的。你家杨花在广东就是坐台呀,未必没对你说起过呀? 是做服务生,大酒店的服务生。新粮道。 凯子就笑:嘿嘿嘿,当然是服务性行业啦,我带出道的嘛。 坐台是怎么个事呢?新粮想起了旦子的话来,心里又抽得慌。 香草接口:坐台就是坐在酒台子上吧?呵呵呵呵…… 凯子点起支烟:实话说吧,坐台就是陪客人喝酒聊天儿,跳舞猜拳儿,陪得人家高兴了给钱儿,知道了吧?老伯。 凯子鬼鬼地笑,香草也鬼鬼地笑。 这不是……卖笑吗?新粮心脏越来越疼。 陪客人嘛,还不是看个人的,你不同意和人家上床,顶多人家只能摸摸捏捏占些小便宜,一天赚取几百块钱来,你不动心啦。凯子讲道理。 新粮就嘟囔:不干净,不干净。 凯子哈哈大笑:人民币比揩过屁股还肮脏,几时干净过? 新粮沉默不语。 凯子道:我堂客菲菲也在坐台呀,现在都职业化了,新粮伯未必还转不过弯来呀?我们是农民阶级呀,赚不到钱只能走这条路子呀,不然怎么脱贫致富哩? 坐台是不是都要陪客人睡觉?新粮盯住凯子的脸。 你要听实话是吧?凯子说:要得畜生钱,伴得畜生眠,不陪得人家开心凭啥别人大把大把掏腰包?我们菲菲,香港老板包一个月就是十万,过后还不是我的老婆? 新粮听到这个数,面上不动声色,心里还是格登了一下。 新粮说:你不是还有生意嘛,收入大着哩。 我带过去的人,一个人收两千块一月的保护费,村里的优惠价一千五,新粮伯你介绍一个我给你一千块,怎样?凯子来劲了。 新粮说:你收一千五?凭什么? 凯子说:不平衡了呀?到那边没有男人罩着你看看……你家杨花我一起只拿了八千元,让她买断了,现在她到哪坐台都自由自在,我管不着。 格狗娘入的,忒黑心哩。新粮心骂道。 新粮伯,我说实在话,杨花长得索利,又还年轻,还应该多坐两年台赚些钱的,现在嫁了,更加不怕什么了呀,已经湿了脚,还不如下海捞个痛快强!哦……呵……凯子打着呵欠,口水流老长。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管他哩。新粮道。 凯子说:你家幺女杨玉不是在县玻璃厂嘛,一月三百多块钱,混命啦?跟我过去一年少不得要赚十万八万的,怎样? 新粮忙说:她还小,还小,才十六,不说这些。 心下却说,给你带过去,月月交你钱,肥不死你! 凯子却看透一样:我也想落个好名声,乡里乡亲仁仁义义,现在兰花、细茹、桂英她们只要一次给我个五千块,买断算了,以后赚多少都是自己的。 哦……哦嗬……我去上个厕所。凯子眼泪汪汪站起身,却从皮鞋里抠了个什么东西走了出去。 新粮说:世道变了。 香草也说:世道是变了。 4, 三天后,杨柳庄的八个男人结伴去广东,不是去打工,是“保护”在外面挣大钱的亲姐亲妹亲侄女亲堂客哩。不过都交了三四五千不等的现金给凯子,长痛不如短痛,往后赚的钱就外人休想拿走一分!我操他娘的凯子,坐在那儿一个月吞掉一千五,杨柳庄做泥瓦工的手艺人一个月汗水摔八瓣也就几百块钱哟,给你赚还不如自个守在那?谁还敢欺负姐呀妹呀堂客呀。 柳家五英亲弟弟还在念初中去不得,但没人罩着也不行啦,想来想去,五英爹春生自个去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春生一年到头也没做什么工。 春生几天后就来电话告诉老婆芹子:挺好的,闺女晚上上班,我就做几顿饭哩,你不要操心喽。 细茹哥也给父母报平安:好着呢,男人们打打麻将,做点饭,神仙一样的日脚!操,早就该来的,白让凯子这猪入的赚了这么多钱! 新粮的女婿旦子工作都不做了,带了老婆杨花和姨妹子杨玉下了广东,这次他想通了:将错就错朝“钱”看!说回来,杨花是黄花闺女会嫁他这个瘸儿? 傍晚,太阳象个盐蛋黄一样搁在后山梁,是杨柳庄人最有味道的时光。村里人几乎都聚在牛栏岗前的大樟树下(牛栏岗当然再没有拴牛了),讲讲古,道道今,男人抽烟,女人织个毛衣。说得最多的当然是猜码了,谁家中了码,自己就会买来些水果香烟槟榔的给大家米西米西,一派农家乐哩。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邮递员李三江的摩托车会在这个时候嘀嘀按响喇叭,老远就喊:杨金宝,八百元;柳宝贵,一千五;杨红光,三千块…… 杨柳庄人会比当年没有遭水灾粮食丰收快活得多了!除了个别没大姑娘的家庭,家家都是笑逐颜开,小康生活就是这样吧? 今天最大的爆炸新闻是李三江念道:杨新粮,一万块! 啧啧啧!杨玉这妮子厉害哩!才几天时间赚格多! 老母狗“憨婆”跳起脚来接汇款单,众人哈哈大笑:这婊子,也想去坐台赚钱哩。 腊梅接到汇票手就在抖动,眼泪在眼眶打圈圈。 新粮走到老樟树后把头碰撞得青紫,他清楚呀:幺女杨玉的“开苞”费哩,十六岁的闺女家就不再是黄花女了。新粮的心口象耙子在反复划来划去,流血哩! 5, 八月,那个早上,太阳刚刚升起来,杨柳庄回来了六个后生仔。 打头两个手里都抱个黑匣子。村里人都出来看:是凯子和他未婚堂客菲菲的骨灰盒! 凯子死了,是注射毒品时倒在厕所里死的。 菲菲死了,据说是下面那东西烂得发臭,医不好了,凯子死了就割脉自杀的。 村里人把两人的坟掘在筲箕坡。往年筲箕坡埋的都是没成家的年轻人,大多是些失身被男人抛弃后喝农药或上吊或投老河死的大姑娘,不过已经成为历史了。 大出殡那天,两具黑漆漆的棺材(里面装进的是骨灰盒和死人衣物)从杨柳村抬出来,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来看,好热闹的葬礼哟。 香草跟在后面,自个儿边撕衣服边吆喝:毒死的,日死的,日死的,毒死的…… 后来哗啦一声,把个奶子显出来,说:凯子,你娘奶水比鸦片烟好吃呀,你来呀…… 香草疯了。 送葬的队伍经过杨柳村小学校时,学生娃娃正在做眼保健操,喇叭里的声音压过了唢呐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眼保健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 我们凝视深渊,如同它凝视我们。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lt/9852.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最新通知化州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临时调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