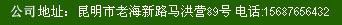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刘文斌预约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ys_bjzkbdfyy/792/ 新邵文学(总第27期) 注:此文刊登于《湖南文学》年第7期 中篇小说 谁在呼喊 文?肖克寒 1 去年农历十月的最后一日,你终于送还了木山冲菊妹子赠给你的“爱华”牌随身听。然后,在腊月里与枫树坳的彩妹子做了订婚酒。然后,娘第一次叫了你“强华”。然后,全家从此都尊呼你为“强华”。 你——我的满弟,此刻正举着把雄性的山斧,劈着个大疙瘩似的枞木树蔸。 你举起手中斧子的时候,差不多次次都要高过头顶。咔——嚓!每劈下一斧好像是在和枞木树蔸决战一个回合,心与力都要呐喊一次。 你只穿件单薄的黑白条纹相间的羊毛衫。直起腰身擦汗的时候,可以发现,你的身高恰与那间披厦屋的门框差不多;壮壮实实又和屋前那棵已长成的小椿树类似。你那脑顶中央的被娘称为“拗毛”的一绺头发老是支起,像是京戏里扮演都督的戴在头上的野鸡翎。 一双大眼睛和圆而微翘的下巴,是从娘那里遗传下来的;两朵颧骨有点外凸,配着条鼻尖有点朝天的鼻子,和老爹有几分挂相。但使你浑身洋溢着一股只有二十来岁的农村男性青年才具有的阳刚之气的,还是那绺“拗毛”。 “强华,强华哎——”娘在披厦屋的灶屋里喊。 娘的嗓子有些沙。但“强华”两个字特别清晰。强华这名字,是你二十岁那年去深圳打工时自己改的。你的原名叫桥保。因小时多病,娘怕你养不大,认了一座石板桥做干娘。你却嫌原来的名字太土气,没有一点男子汉派头,当然也跟你喜欢歌星“德哥”很有些关系,尽管现在又喜欢上了另外一个歌星。你最乐意接受的是你那帮小兄弟叫你“华哥”。只要叫你几声“华哥”,嘿嘿,你可以把脑壳给人家当凳坐。 “强华哎——”娘又在喊。平时,娘叫桥保叫惯了,总也转不过口,被你“飙”过几回:“只管桥保桥保,我又不是三大两岁!”娘虽然还是不太转得过口,但碰上要紧的事,已经学会喊“强华”而不叫“桥保”了。 你对娘的进步当然满意一些。娘第一次叫你“强华”的时候,就让全家感到你不再是家里人人可以小看的男性公民了。遗憾的是,一年后的今日,当娘叫着“强华”的名字的时候,你却不得不去枫树坳彩妹子家“算账”,也就是与彩妹子“一刀两断”了。“算账”是我们这乡里的规矩,男女双方在媒人和证人的监督下,亲自到场结算以往的人情经济,然后才算正式断绝关系。 乡里千样万样变了,这一样,就是没变,有时比法律还管用。 尽管是年下了,账却不得不算。 其时娘又叫了一声。这一声叫的却是“桥保”。但你这一次没有“发飙”。只是犹豫了一刹,那双大眼睛里分明掠过阵阵无奈:娘老了。 你撂下斧子,用脚把杂七杂八的柴禾踢成一堆后,脱下那双磨得有些破烂的手套,循着娘的叫唤进了灶屋。 屋子里,可能是柴火没有干透的缘故,缭绕着一些呛人的烟雾。 娘和老爹都在灶屋里。娘从佝坐在灶头的老爹的手中接过一个已经摩挲得陈旧并撕去好些页张的绿色塑壳笔记本,交给你看。你知道上面记着些什么,并不去接,只瞥了一眼,那神情有点空。老爹是个人精,独个儿念念有词,像是提示给你听:“共吃酒席四次;送节礼两次,其中端午节一次,中秋节一次;为女方家开瓦厂到乡政府跑关系用黄梅烟两条,软壳的…… 娘嗓音有些沙地说:“强华哎,还、还有么?要记清楚哦!” “记清了,记清了,前五百年就记清了!”你挠了挠后脑勺,有点厌烦,但这次忍住了没有“发飙”。“五百年”是你从老人说的“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话里化用过来的。 你有点焦躁地把那件搁在灶屋大凳上的印有香港某巨霸歌星头像的灰褐色夹克三下两下地套上。 娘又说:“你们私下里还、还有么?喝杯茶算杯酒的规矩你也要晓得哦——人家会请高手哩!” 你真有点想“发飙”了,更不耐烦地打断娘的话:“晓得晓得,反正又不是……”你说到这里一时找不到个妥帖的词,不禁望了老爹一眼,见老爹把烟斗从左嘴角换到了右嘴角,烟管被咬得“咯”的响了一下,脸色也比烟斗里的烟缕还青,就呐呐地住了口。 娘说:“要算就要、要算干净,算出本事来!以后还要找老婆呢。” 这是娘要叮嘱的最重要的那一句。 算账能算出什么本事来呢?这时候你才突然想起刚才未能想出来的词:“打抢”。你立即否定:这不是“打抢”。 “吃了饭再过去。咳,也不要太早么……”老爹精精地说。 “唉,回想一下,都是计呀!”老爹又说。见老爹的脸色更青了,见娘那发白的头发在窗口边亮了又亮,像是一蓬经了霜的白菊花,你的眼皮方才有点忧郁地垂下来,转身进了正屋去自己的房间。 在房间里,你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塞进上衣的内袋,一边抬着头东瞅西望,像是一头被绳子绊住的牛,两只脚提也不是,立也不是。 “靠!”你低声骂了一句,终于跨出了墙上贴有歌星彩照的房间。那烦躁的神情,分明是心里还有一桩大事儿搁着。 你心里的确还有桩大事儿搁着。在你看来,这桩大事比起你跟彩妹子算账的事要重要得多。 为了这桩大事,一连几日,你的鞋底差不多把花屋院子通向花屋学校的那条石板路都给磨光了一层。 说来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过是等一个好兄弟的电话而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蜗在旮旯里的花屋村可不是通讯畅通的时代。 2 就这样犹豫着,你一步一步挪近了那家夜宵店。 晚上八点左右,南方城市的这条小街上,车如流水人如潮。你处在潮的一边,像一粒被淘汰的沙子,落寞,甚至有点猥琐。你现在最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文壮伟父亲
- 下一篇文章: 旧上海名门望族的海派大宅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