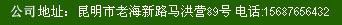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同样的命运(一) 文|鹿松林 图里河镇的大字报贴得很红火,不仅镇里人看,还引来了镇外很多人来观看学习。 人们亲情上很多东西丢失了,揭他人隐私,探别人过去,造他人谣言,把别人上纲上线。其实大字报的较量,只是“文攻”。大人们接着进行了“武攻”。 老林子里当时两大派,一个叫“红色造反者兵团”简称“红色”;一个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司令部”简称“革造”。这两个组织分别由若干个观点一致的小组织联合起来的。 “红色”的成员,大部分是山下一些机关直属单位的人们,“革造”是山上伐木队和林场的人们。这两派手中武器是大木棒和石头,今天你围攻我,明天我回攻你,打打杀杀,还死过人。 这两派的人们,当时都喜欢唱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革造”的工人大都没有文化,是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的“老跑腿子”,这是一群家在关内,常年跑来跑去的人。他们有一段被定为是保皇派。被“红色”打到深山老林子里躲起来。 我当兵之前,“革造”才被重新定为是革命群众组织。“革造”不服“红色”啊,把自己的招牌用焊枪焊死在政府大门对面,标示自己也是革命的,说什么也不许摘。 来林区支左的是一支铁道兵,后来新来了一支边防部队。林区地盘太大太长,每个镇来的支左头头就是个基层的干部。一位干部转业时在这里当了武装部长。他与这里一名女广播员有染,女的要坚决嫁给他,他又不能离婚,就掏出手枪打死了女广播员,自己也自杀了。 老林子的领导机构为了解决职工家属的冬春两季饥荒,在荒甸子上建了许多农场。这些农场生产粮食、羊肉、牛肉、土豆和一些蔬菜,这些物质到了秋天,由林业局分别补给山上或山下的职工和家属。 作者库都汉老屋原址,如今绿草青青,生机再现。 同样的命运(二) 图里河有三个农场,分别为一农场,二农场和三农场。我中学一毕业,先是分配到三农场当知青。这次一起走的不光是我们黑帮子女,文革中的红卫兵们也都在车上,没想到大家是一样的命运。 黑帮子女的心态比较平和,面对这种命运心境已经磨练出来了,而是风风火火的红卫兵脸上有些很麻木。 到了农场,并没有什么人接我们,下了汽车,自己找自己的行李,按着贴在墙上的名单和帐篷号码,自己扛着行李找自己的床位。我在账蓬里看见了同班级和大我一、二年级的红卫兵战士,他们和我睡在一张通铺上,吃着一锅饭。 刚进账蓬的时候,大家闹哄哄地打着招呼:“你也来了?” “嗯,你还好吧?” “糊里糊涂吧。”大家都是很无奈。 我放下行李,悄悄地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当时心胸有些不地道,蹲在一旁想着红卫兵当年的威风。 我们刚到三农场,住的是帆布做的大帐篷。一个大帐篷能住三、四十人。床铺是木板架起来的,上面铺上干草,把行李再铺上就睡觉了。到了冬天,帐篷里支上用空油桶做的铁炉子,里面放进木柴烧起火,帐篷里也很暖和。两年后,我们自己从山上运来原木,自己用原木垒起了刻楞房子。 三农场的活儿很杂。 春、夏、秋种地,种小麦、土豆和大头菜。 这里的土地广阔,一条垅至少有一亩地,长长的,这头看不见那头。夏天用锄头铲地,上午一条垅,下午一条垅,我们身体弱小的,下午半条下午半条,一天也就是挣十个工分,一个工分也就是一角钱。 这里的小麦一般是用机械种,机械收。有的年头也用手镰割,这时候,累得好像腰都要断。 这里,也有成群的马,成群的牛。负责看马棚和牛棚的职工和孩子,他们都住在知青点下面的刻愣房子。他们负责骑马儿放牧,到了秋天,知青们跟着农业工人扛着大扇刀去荒甸子上打草,这草就地晒干了运回垒好,备冬天给羊和牛吃。这个打草季节是近一个月时间,要天天打,抓紧打,打不够数,牛羊是无法过冬的。 到了冬天,整个农场,不分农业工人还是知青,全部上山帮助伐木队伐木集材。这里说是帮助,实际上要和林业局结账的。 当年,库都汉林场俱乐部现状,本文作者儿时的艺术舞台。 同样的命运(三) 冬天是农场收入的一个黄金时间。冬天也是老林子里各林区的生产黄金时间。 冬天这里的松树、桦树、杨树、樟树,包括所有的树木都不生长了,树里树外被寒冷的天气冻着,一根根脆生生的。树里的树汁、树油都冻成小冰渣儿,用斧子砍,树干一斧一个大炸口;用油锯一拉,一拉一寸深,工人们干起来非常痛快。 天气一冷,树枝、树杈就冻得更脆了,树一放倒,树枝树杈早就砸的断了几节,残余的一些,我们年龄小的,就用雪亮的斧头一敲或者一砍,全脆生生的顺着树干断的平平的。 树木被修成光溜溜的树干,林子里的行话叫“原木”。这些原木一根一根由人和牛儿集运到山下的公路旁,由另一组人装上“拖拉机”和“塔拖拉”,再运到山下通铁道轨的储木场装上火车。 用牛儿集木材,是一头牛拉一个特制爬犁,一个爬犁上绑一根原木。一头牛爬犁由一个人负责赶,人和牛延着开出的山道,把原木往山下拖,如果刚开始没有山道,那就要跟着有经验的人往下趟。 沟里的冬天,天寒地冻,春夏秋三季的水沟、水洼、沼泽地全冻住了,到处是冻得邦邦硬的雪地,平平的、滑滑的,牛拉起爬梨,拖上一根原木畅通无阻;有时从陡陡的山上往山下拖原木,人、牛和爬犁三位融成一体,又穿树空,又防陡坡,来回一次也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位姓阎的知青,下乡前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胆子大、爱出头。头年冬天,他自报奋勇赶着牛爬犁,拉着原木走前面,想给大家趟趟路。工人师傅开始不同意,他向领袖表决心发大誓,人家就随着他了。他用的是一头两岁的小牤牛,黑身白面,生性犟货。两个性情相同的搭档,人叫牛吼,顺着树空往山下奔。哪知道,还没到山的一半,爬犁翻了,牛的两个很漂亮的犄角都断了,站着的牛儿,鼻孔一张一张喘着粗气,白色的牛脸溜着红血。一屁股坐在雪窝里的曲知青,满头热雾,双眼无神,一顶狗皮帽子被他自己抛到很远。 工人师傅说,这是人、牛跑毛了,小牤牛一头撞在树上了。队里要处理他,怎么处理呢? 队里先让我们知青讨论一个意见,大家两个晚上谁也不说话,“红卫兵”们不说,“狗崽子”们也不说,后来,这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同样的命运(四) 拖拉机,塔拖拉运起原木,是十几根装一车,到什么道路上都是平坦无阻。 没有来过老林子里的人,一想起冬天,就都会想,这么冷的天气,人在荒野怎么干活儿? 这就错了。 冬天里,在老林子屋外干活儿,是最出活的。你想想,人不干活儿,身体就要受冻啊。 这里的工人夏天发单劳动服装,冬天是一身厚厚的棉袄、棉裤,加上带毛大头鞋,松软的棉胶鞋、棉手套,皮靴子,你就是全都穿上,冬天在外面不干活儿,也要冻得“嘶嘶”“咯咯”的。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到山上作业场,先脱下国家发的皮短大衣,再脱下棉上衣,只穿里面的绒衣或小薄棉袄“呼哧呼哧”,干上一小会儿就出汗了。 林子里的人喜欢冬天这样干活儿,痛快、实在,真爽! 我们知青分农业队一些儿,去牧业队一些儿,冬天都集中赶到山上。 我先是在场部赶牛车拉水,一天十几趟,牛车上用一个两节油桶焊成的大水桶。 我和牛在山脚下的泉水边把水运回来,要上、下午分别把食堂、宿舍的水桶全装满。我的牛是一头健壮的牤牛,它很有力,走得快。我先要用小水桶一下一下把泉水装在车上的大水桶,到了食堂或各个宿舍,再把水从桶下的一个水管里放出来,再用两个小水桶一桶一桶的倒进各个房间的蓄水桶里。 我最怕过休息日,女知青、男知青用水多。我不同意他们在宿舍洗衣服,我请求他们去山边小河流去洗,时间一长,他们都同意了。其实,他们都让着我,我太小,他们不同意,我就死活不拉水,尤其是下雨天,尊友只好代替我去拉水。 “红卫兵”与“狗崽子”,在同样的命运面前,磨合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共患难了。 同样的命运(五) 我也参加过春天种土豆和秋天起土豆。 春天我们要早上六点就起床,半个小时洗脸吃饭,半个小时赶到地头,地头的拖拉机已经在轰鸣着,是清一色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不是南方的手扶拖拉机。我们每天不早起,中午前就干不完一条垅上的活儿。中午是一点就要出工,晚上六点回来。春天种是这样,夏天铲地也是这样,秋天收土豆时间更紧张,要把土豆抢在头场雪前从地里起回来,否则天一冻地,土豆就不好保存了。 一到秋收,土豆地全是人,连附近的中学老师都要带来学生参加秋收。 牛儿拉着犁杖,把土豆垅一划开,人顺着犁头两边一看,又白又胖的土豆一下子全露出土面了。三农场的土豆地是沙土地,种出来的土豆不沾土不带泥,又白又大又沙又面,很是好吃,是老林子里出名的。 这时候,天一亮我们就上班,晚上看不见土豆了才收工。 苦是苦,累是累,收自己用汗水种出来的成果,还是能挺得住,只是半夜回来躺在床铺上,伸伸酸得要断的腰才偷偷哭出来。或是骂几声脏话。这时候,文革的躁动痕迹已经离这里的人们远去。知青们已经开始积蓄着自己人生另一个记忆。 林彪元帅飞机出事了。人们感觉人生有太多的难料,太多的日鬼。老林子的知青已经不太关心大山外的折腾,年龄大的稳重起来,年龄小的就该玩玩我的。 我学会了骑马,马儿是一匹小红马,它有一脖子很好看的红马鬃,奔驰起来,所有红鬃往后一飘,像是一团火。 我跟车老板赶过大马车。老板曾经是个有道行的人,只有年月已经不是曾经属于他的年月。他只有弯着腰少话的份。他很会扔石头,拿起一块石头,瞄上前面的树干扬手甩出去,肯定手手打中。我不会去问老人过去究竟做过什么,因为我心里是扭曲的,也应该说是单纯的。 他是我的师傅。 当我的功夫见长的时候,师傅就带着我到他知道的长满灯笼果的地方,我们摘着灯笼果,大口大口的吃着。他看着我,我冲师傅笑着,我仿佛觉得自己像土匪。 我们哈哈大笑,管你春夏秋冬……。 人哪,其实还是选择对自己生命和活着有帮助的人,太多理想跟百姓活着没什么……。 作者授权请勿转载来自:正清和文化 编辑|亚男 长按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价格北京白癜风治疗医院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上海滩名门望族的大宅院和它们的传奇故事
- 下一篇文章: 艾尚影吧最新推荐树大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