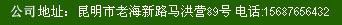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STORY 风飘石,原名张绪平,现供职于瑞昌市人民政府。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梦呓》、《自杀的树》。 追捕一粒叛逃的肉丸子 一 庚子年的端午节正向我们走来。六岁的我天天坐在青石的门坎上数着日子,等着端午的粽子和煮蛋。 父亲是生产队长。农历四月底的一天,他到县里去参加四级干部大会,回来的时候天已墨黑。一家人围着油灯喝菜粥,父亲一边转着蓝边碗吸粥,一边给我们传达县里的四级干部大会精神。他说,好了好了,中央来了精神。地委开了大会,专门研究了管好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县委今天传达了地委的会议精神,苦日子就要到头了。最后,父亲把蓝边碗扣在他的脸上,像一匹饿狗一样伸出他的舌头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又用他宽大的手掌抹了一把嘴,就在饭桌上宣布了一个伟大而振奋人心的决定:端午节就要来了,今年一定要过一个像模像样的端午节。 父亲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第二天的晚饭桌上,父亲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他卷“喇叭筒”烟的竹纸,隆重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安排的庚子年端午节的食谱清单: 肉丸子10粒 鸡蛋6枚 粽子7只 父亲十分庄重地向全家人做了宣布,就像他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宣布队上的事情一样认真。肉丸子是这样分配的:姐姐、我、弟弟每人两粒,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各一粒。粽子全家每人一只。关于粽子父亲还做了特别的解释,吃糯米粽子是不可能的,到哪里去找糯米呀?但是端午节不吃粽子就不叫端午节。到底吃什么粽子呢?父亲说,到时候自然就晓得了。煮鸡蛋是姐姐、我和弟弟每人两枚,一枚在端午节吃,另外一枚要用胭脂花染红,由母亲用棉线织成网兜套着挂在我们胸前,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对于我来说,能够作主支配一枚鸡蛋那真是一个比天还要大的喜悦。 我看见,在油灯的映照下,母亲的眼睛放出绿光来。之后,她忧虑地说,到哪里去买肉丸子和鸡蛋呢?就算买得到那又要花多少钱呢? 父亲满怀信心地说,我有办法。 祖父也对父亲说,春生,几个细伢崽苦足了,真有办法是要过个像样的端午节。 自从父亲宣布了那个决定,日子过得特别慢。我天天坐在青石门坎上等着太阳快些落山,等着那个有肉丸子、鸡蛋和粽子的端午节快些到来。 在五月初三的晚饭桌上,大家还没有开始喝粥,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向全家人展示了他的杰作:十粒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煮熟的肉丸子,六枚鸡蛋和一布袋糙米饭。父亲提起那袋糙米饭说,我们吃不上糯米粽子就吃糙米饭包的粽子。看见那些傲慢的肉丸子和鸡蛋,我的嘴里立刻涌出许多涎水来。 母亲是用干萝卜丝炖肉丸子。我们都吃完了自己的肉丸子。只有父亲和母亲的肉丸子还在瓦钵里跳荡。祖父和祖母总是催促父亲和母亲说,你们吃呀,你们快吃。母亲用她的筷子在瓦钵里不停地翻抄,说,不急不急,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父亲也不停地附和着母亲。他们是想让全家人在剩下的萝卜丝里尝到更多的肉味。在快要吃好的时候,父亲终于站起身,用他的筷子在瓦钵里翻找,最后他说,咦,怎么只剩下一粒了呢? 母亲说,我吃了一粒。 父亲说,你什么时候吃了一粒? 母亲又说,是不是你少买了一粒? 父亲一边不停地翻找一边说,没有,我买了十粒。我们排两次队买了八粒,用黑市价买了两粒。 我立刻低下头,不敢看父亲和母亲。 我听见母亲用她的筷子敲了一下父亲的筷子说,莫找了,可能是我碗橱没关紧,不是被猫吃了,就是被老鼠拖走了。 父亲犹疑地哦了一声,便夹起最后的那粒肉丸子放进母亲的碗里说,你吃吧,一大家人都靠你操持,总是撇汤吃菜,一年到头也见不到荤腥。 母亲又把那粒肉丸子夹还到父亲的碗里说,你吃,耕田耙地的,重事都是你做。 父亲再次用他的筷子夹起那粒肉丸子说,我每年都到县里和公社开次把会,队里有时也来个把客,一年到头还见得到次把荤腥,还是你吃。母亲立时用筷子拦住,两个人推来推去。这时,那粒一时找不到归属的坚硬的肉丸子忽然就有了叛逃的企图,只见它快速地从父亲的筷子上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终于逃出了死亡囚笼的囚徒,再奋力地一跃,顺势就滚进了墙角的鼠洞。 母亲用惊悸的目光看着父亲,满眼的愧疚。 父亲也用愧疚的目光安抚母亲。而后,他立时端起油灯来到鼠洞边,撅着他雄健的屁股,将他的筷子伸进鼠洞反复地掏夹。可是那粒叛逃的肉丸子似乎在一瞬间便逃得无影无踪。不甘失败的父亲放下筷子又从大门旮旯里拿来一把锄头,顺着墙角挖。母亲掌着油灯为他照明,见父亲挖了一尺多深也没有挖出那粒叛逃的肉丸子,便说,这回怕真是被老鼠拖走了。沮丧的父亲只好收起锄头说,算了,明天再说。 二 那粒叛逃的肉丸子不是一粒简单的肉丸子,那是一粒来自“东方红”号轮船上的身份不一般的肉丸子。住在长江两岸有些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东方红”号轮船是长江内河上的客轮,总共有上十艘,上至汉口,下到上海交替着不停地穿梭。庚子年间,物资匮乏,很多东西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饭馆里吃饭要粮票,点荤菜要肉票和鸡蛋票,就连做饭生火的火柴虽然只要一分钱一盒也要火柴票,只有“东方红”号轮船上的饭菜只要钱不要票。为了吃上一碗不要粮票的饭,大家都愿意花五角钱买一张湖北广济到江西九江的船票,到“东方红”号轮船上去吃一碗不要粮票的糙米饭,晚上再带一碗回家给家人共同分享。 为了庚子年的那个“像模像样”的端午节,父亲自从做出庄严的承诺之后,便与母亲和姐姐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父亲每天收工之后就上山去挖树兜砍片柴,母亲和姐姐每天都上山去耙松针和拣干松果。这三样东西是广济县城里的“街上人”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广济县城里的“街上人”每天做饭都要生煤球炉子,只有底下铺一层松针,再铺一层干松果,再架几枝片柴才能引燃石头一样的煤块,否则一天都要饿肚子。那些天母亲和姐姐每天都各挑一担松针和松果到广济县城去换钱。 五月初三的早晨,父亲开始践行他伟大计划的关键环节。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叫醒姐姐。父亲挑着满满两柴夹的片柴,十一岁的姐姐也挑着两麻袋干松果,摸黑走十几里山路,为着那个“像模像样”的端午节去做最后的冲刺。他们在天亮之前把片柴和松果送到主家,趁着“市管会”的人还没有上班,花六块钱在黑市上买了六枚鸡蛋。这都是几天前就约好了价格和交货地点的,就和现在黑社会的毒品交易一样神秘。父亲把鸡蛋放在铝皮饭盒里再藏在怀中,就去买了一张半广济县到九江的早班“东方红”号轮船的五等散席船票。少买半张票能节约两角五分钱。父亲反复地叮嘱姐姐检票的时候要屈着膝盖。这天早上,父亲带着姐姐忍着饥饿站在“东方红”号轮船的前甲板上,看着东方慢慢地红。县里开会了,要让群众过好生活。父亲的心房里涨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对姐姐说,要买到肉丸子就要早点排队。按照轮船上的规定,每人每餐只能排一次队买一份饭菜,买多了就是投机倒把。买完饭菜后船票上还会被卖饭的厨师用红笔划上一个勾。细伢崽排了队也只能买半份饭菜,父亲又反复地叮嘱姐姐,排队买饭的时候一定要踮起脚来像个大人一样。 午饭的时候父亲和姐姐两人分开排队一人买到了一份饭和两粒肉丸子。他们把肉丸子装进饭盒,一人吃了一份寡饭。这已经是他们对自己最奢侈的犒劳。下午他们再分开排队一人又买到了一份饭和两粒肉丸子,但他们什么都没吃。之后,父亲再用黑市的价格在别人手里买到了两粒肉丸子,这才凑足了十粒。他们从九江下船再坐车回家已是掌灯时分。 五月初三的晚上,父亲和姐姐凯旋而归。从此,那十粒肉丸子便来到我家,像从外婆家来的尊贵客人一样,躺在一只蓝边碗里,被我的母亲郑重其事地摆放在碗橱的顶格,等待着庚子年端午节的到来。那天夜里,我就像惦记着不舍的玩伴一样惦记着碗橱顶格的那只蓝边碗,激动得无法入睡。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在上弦月的清辉之下,我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拉开碗橱,端出那只蓝边碗就着月光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地闻。我的喉间快速地分泌着唾液,慢慢地充满了我的口腔。我不受管束的手鬼使神差地翻出了最底下的一粒,掰下蚕豆大小的一块快速地塞进了嘴里,然后再用拇指和食指去弥合那粒肉丸子身上的创伤。 第二天上午和下午,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又如法炮制。到了晚上,再一次端出那只蓝边碗,看到那粒肉丸子已由一只乒乓球变成了一枚麻雀蛋。我一时头脑晕眩,捉起那粒麻雀蛋大小的肉丸子就塞进了嘴里。 就这样,我分四次偷吃了一粒肉丸子。 如今我想,与其说那是十粒肉丸子,倒不如说那是十粒淀粉丸子。每粒虽然都有乒乓球大小,但是因为并没有多少肉而十分的结实,似乎就像是真的乒乓球一样能够在桌面上反复地弹跳。 三 父亲放下锄头,坐回到饭桌上,就着油灯专心致志地卷好一支“喇叭筒”,用一枝麻杆从油灯上借过火来,一面吸着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八角钱一粒。 父亲一米八十的身高,孔武健壮,犁耙磙耖样样娴熟,是拿十个工分的壮劳力,又当着生产队长,每天另外再加记两个工分,一个劳动日拿十二个工分。那个时候,一个工分值四分钱,父亲一天的劳动收入是四角八分钱。一粒肉丸子差不多就是他两天的收入。他十分心痛又无可奈何,只能对着鼠洞发呆。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民兵,剿过匪,后来又在朝鲜当兵。因为他孔武有力,当的是侦察兵,每天的任务就是捉俘虏抓舌头。这两段经历养成了他浓厚的追捕情结。那粒叛逃的肉丸子不仅仅只带走了他近两天的劳动收入,更重要的是还带走了他对母亲的一片温情和我们这个家庭的共同欢乐,真是罪不可赦。父亲暗下决心,决不放弃对这粒叛逃的肉丸子的终身追捕。 执着的父亲不肯入睡。他把油灯拧得碗豆一样大小,坐在饭桌前双目如炬盯着那个鼠洞。半夜子时,父亲对着那个鼠洞开始喃喃自语:鼠大仙呐鼠大仙,今年是你的本命年,现在正是你主事的时辰,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你世世代代都在我家过日子,娶妻生子,嫁女接媳。我们一不放夹,二不投药,相安无事,让你一家过着妥帖的日子。你要是真有灵气的话,千万不要吃了那粒肉丸子呀。你要是吃了,全家老小就莫想再在我这里过安生日子了。 疲倦的父亲在似睡非睡之间,似乎听到了吱吱的鼠鸣。他睁开惺松的睡眼,果然就看见一只五六寸长的硕鼠端坐在鼠洞边,只见它睁着一双豆大的黑眼,双手合在颈前对着父亲友善地笑。接着后面十几只大小不一的老鼠自鼠洞中鱼贯而出,它们衔草驮粮,扶老携幼,像是要搬家一样逶迤而去。之后,那只硕鼠用它的双手在脸上抹来抹去,仿佛是要告诉父亲,它们并没有吃掉那粒肉丸子。父亲相信了它们。 第二天中午,父亲收工回来,再次拿起锄头,重新开始了对那粒叛逃的肉丸子的追捕。挖到两尺多深的时候,父亲终于看见那粒叛逃的肉丸子颓败地站在枯草构成的鼠窝边。这粒罪不当赦的肉丸子为了伪装自己,浑身已长满了茸茸的白毛,显出一幅委屈的样子,让父亲感到十分的陌生。父亲伸手捉住那粒叛逃的肉丸子,举在眼前反复地审视,在验明了正身之后,他终于充满胜利者的激情骄傲地说,我看你往哪里跑!在灶间煮粥的母亲闻言而至,看着立在父亲拇指和食指上的那粒陌生的肉丸子而不知所措。她看见父亲用另一只手去拔那粒肉丸子身上的白毛,那粒叛逃的肉丸子立时便显出萎靡来。父亲把褪净白毛的肉丸子凑近鼻子,嗅了嗅说,馊了。 母亲立时惊恐万状,尖声叫道,馊了不能吃! 父亲像在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对母亲的尖叫充耳不闻,只是反反复复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那粒叛逃后又被重新缉获的肉丸子。良久,父亲回过头来面对母亲说,你身体不好。我身体健得很。放到肚子里最妥帖,不能吃我不吃,我吞。话音未落,只见父亲的喉结一滚,那粒被重新缉获的肉丸子像昨天滚进鼠洞一样,快速地消失在父亲的喉间。 母亲瞪着惊愕的双眼,说不出话来。 四 庚子年的端午节,父亲终于吃了一粒肉丸子。尽管那粒肉丸子姗姗来迟,尽管父亲说他不是吃而是吞。但不管怎么说,那粒企图叛逃的肉丸子是实实在在地进了父亲的肠胃。父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是全家人的主心骨。要不是父亲的英明决策和坚定不移地践行,在庚子年间,我们怎么能过上那样一个有肉丸子、鸡蛋和粽子的端午节呢?在那个庚子年的端午节,父亲终于也“吃”上了一粒肉丸子,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十分的欣慰。尤其是我,偷吃那粒肉丸子的罪恶感消逝了大半。 晚上喝完菜粥之后,父亲照例就着油灯吸燃一支自卷的“喇叭筒”香烟。灯影下,我看见父亲露出祥和慈爱的面容,好像是要对庚子年的这个端午节作些总结。我更加如释重负,并且立时有些轻佻。果然,当父亲又吸完一口香烟,便转向母亲愧疚地说,真可惜,就你一个人没有吃上肉丸子。 我喝了很多汤。母亲说。 母亲话音刚落,就见父亲双眉微蹙,面露痛苦的神色。母亲关切地问,你不好过吗? 要拉屎,屁眼头像有蚂蚁在爬。父亲说。 在庚子年间,拉屎可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憋着舍不得拉。如果你轻易就把直肠里的屎拉出来,一定会饿得更加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说不定还会刚系上裤子就一头栽倒在地,从此不再起来。父亲自然是也舍不得去拉。于是,他一边吸烟,一边反反复复地提肛。 但是,谁也想不到,那粒肉丸子确实不是一粒简单的肉丸子。它法力无边,仿佛就是孙悟空变的一样,在父亲的肚子里搅得他不得安生。隔着桌子全家人都能清楚地听见父亲的肚子里就像是有一扇石磨在空转。在母亲担忧的目光里,父亲终于憋不住要去上茅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抬起屁股刚要站起来的时候,父亲的直肠变成了一支真真切切的喷射的水枪。 油灯下,父亲羞愧地低下了他的头。 那天晚上,我惊恐地蜷曲在被窝里,黑地里瞪着双眼,用耳朵捕捉父亲房里的一切动静。 父亲不断地急促地跑厕。在跑厕的间隙里,父亲和母亲有断断续续的对话: 父亲:想不到拉得这么狠。 母亲:吃坏了那粒肉丸子。 父亲:我没吃,是吞的。 母亲:到了肚子里都一样。 父亲:我只想到你是吃不得的。我身体健,不怕。 母亲:铁汉也架不住三泡稀。 父亲:哎,我想就是块石头吞到肚子里也能塞塞角。 母亲:现在好哦,黄瓜打锣。 父亲:是哦,统共几粒米,全拉了。 母亲:喝点盐水吧,喝了会好些。 喝了盐水的父亲并不好,反而跑得更急。母亲便提来一只粪桶,放在父亲的床头边。 便听见水枪时不时地往粪桶里劲射。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的房门吱呀一声,大队合作医疗的火根叔来了。就听见火根叔说,这是土霉素,一天吃三餐,一餐吃两粒,头餐可以吃四粒。 母亲倒水。 父亲吞药。 狗在村巷里急吠。 猫头鹰在后山上呜呜地哭。 我担心父亲可能会死。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才在恐惧中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 第二天我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父亲的房门前。我想到父亲可能会死,便不敢走近他的床前,只是站在门槛上双手搂着门枋用惊恐的眼睛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父亲也用无力的眼神看着我。我想这都是因为我偷吃了那粒肉丸子闯的祸。不然的话,父亲也不会因为那粒叛逃的肉丸子和母亲推来推去。如果有两粒肉丸子,父亲和母亲一人一粒,那粒肉丸子也就没有了叛逃的机会,父亲就不会病成这样。我想要是父亲死了,父亲的鬼一定不会饶恕我。我越想越怕,不由自主地就哭了起来。 父亲看见我哭,便向我招手要我过去。我看见父亲的手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粗壮。他的脸上也失了血色,眼窝深陷,呼吸急促而低微,腹部平塌。我想,躺在床上的是不是已经就是父亲的鬼呢?我要是过去,父亲的鬼一定会捉住我不放,我吓得转身就跑。 早饭过后,母亲接来大松伯给父亲诊病。可是,我看见大松伯连只合作医疗的药箱都没有,手上只拿着一块两寸宽三寸长的竹板。祖父过来帮着大松伯扶起父亲来。大松伯就蘸着母亲手上碗里的茶籽油,用那块竹板在父亲的肩颈、背脊、前胸、两腋、肘弯和膝弯处不停地刮,就像是屠夫给宰杀的猪褪毛一样的卖力。我长大后知道了那叫刮痧。 但是,父亲的病情并不见好转。他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低沉而微弱地呼吸,塌陷的腹部像一只浅浅的长长的撮瓢。我想父亲可能真的会死。 第三天,大队合作医疗的火根叔带来了一个穿白长褂的人,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四十来岁,戴着眼镜,胸前挂着一颗由两根黄胶皮管子连着的白铁饼子。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听诊器。他先是坐在父亲的床沿上给父亲把脉,再把那个白铁饼子贴在父亲的前胸后背上下左右地听,然后翻开父亲的眼皮用一支手电筒去照。做完这些之后,他把父亲床头的那只粪桶提到屋外,对着日光边荡边看。回到屋里后,他对火根叔说,是霍乱,要隔离。 怎么隔离?火根叔问。 隔山无用要隔水。眼镜医生说。 经过眼镜医生、火根叔和大队支书的商量,当天下午,父亲躺在一架翻转的竹床上,被抬过青竹溪,安置在大队林场的一幢废弃的屋子里。 五 父亲要被抬过青竹溪,母亲死活不肯,拉着那架翻转的竹床不松手。眼镜医生说,这是传染病,放在家里,弄不好不只你死,伢崽们也会死,全村人都会死。母亲立时被眼镜医生的话击倒,不由自主地就松了手,看着父亲被四个年轻人抬着,跨过那座板桥,过了青竹溪。 父亲被抬过青竹溪后,家里变得空空荡荡,自此我便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不敢去见父亲。大人们也不准我们去见父亲。只有母亲和火根叔可以去见父亲。火根叔每天去给父亲吃土霉素。母亲则是按照眼镜医生的吩咐,每天用一只瓦罐熬绿豆叶子汤去喂父亲。没有几天,生产队的绿豆叶子都被母亲撸得精光。但是,坏消息还是不断地由母亲从青竹溪那边带回家来: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眼睛都定了珠了。 已经没有什么脉象了。 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火根叔再也不去给父亲吃土霉素了。但是,母亲还是那样锲而不舍,每天清晨她便提着那只瓦罐,走过板桥,消失在清竹溪对岸的丛林里。终于有一天,母亲回来后,没有言语,只是呆坐在堂屋里流泪。之后,她站起来掸掸衣襟,抿一下头发,便走进房间去收拾父亲的衣服。祖父和祖母从母亲的行为中读懂了许多。祖母也来到房间帮助母亲一起收拾。祖父背剪着双手走出大门,召来两个叔伯侄儿,从回马楼上放下一具棺材来。 那是一具二十筒的杉木棺材,是父亲在几年前为祖父或祖母准备的,白皮的,还没有油漆。我的两位房叔用两条长凳搁起那具棺材,掸去上面的积尘,再用刮刀反复地刮,然后到小学堂里去讨来两瓶墨汁,充着油漆刷在棺材上,不到一个时辰,那具棺材便已黑白颠倒。 祖母和母亲按照“上五下七”的风俗给父亲准备寿衣,浆洗好晒在门口的竹篙上。邻舍们看见便来关心地问。母亲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 看着那具搁在条凳上的棺材,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想象着父亲将被怎样地放入那具棺材,将被怎样地盖上盖子,将被怎样地抬出家门,又将被怎样地埋入土中。然后,父亲的鬼什么时候回到家里,他又将对我说些什么。我想父亲的鬼是定然不会饶恕我的罪过的。 就在那天夜里,雷电交加,突然下起暴雨来。电闪雷鸣的时候,透过屋顶上的亮瓦,我看见了苍白的天空,天空中仿佛有父亲的双眼,幽怨地注视着我。那滚滚的雷声仿佛就是父亲难舍人世的倾诉。在雷鸣的空隙里,我听见了母亲的房间里传来嘤嘤的哭泣。惊惧就要让我的心脏裂成两半。我奋不顾身地跳下床来,赤脚跑进母亲的房间。电光之下,母亲也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床来,把我紧紧地揽进她的怀抱。母亲不断地拍着我的后背说,我儿不怕,我儿不怕。 是我吃了那粒肉丸子。我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说。 我儿该吃,我儿该吃。我儿吃了易长易大。母亲还是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后背。 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拍打堂屋的大门。母亲也听见了拍门的声音。我和母亲屏息谛听,分明就听见是父亲微弱的声音:开门,开门。我是春生。 这时,我看见祖父和祖母掌着一盏油灯,披衣走了进来。我们只用眼神做了交流,便共同再次屏息谛听,又听见大门外的父亲拍打着门环:开门呐,我是春生。 祖父说,是春生。便带着我们绕过那具棺材来到门边。祖父问,真是春生? 大,是我,是春生。 祖父的手立刻颤抖起来,油灯在他的手上不停地晃。祖父用另一只手去拔门闩,怎么也拔不开。那件披着的夹袄从他的肩头滑落了下来,堆彻在那具棺材的头前。 当祖父打开大门的时候,风停雨静,皎洁的月光照得大地一片银白。我看见父亲像麦地里驱雀的草人一样立在门口。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鸡鸣。 父亲摇摇晃晃地走进门,看见那具棺材,对母亲说,这是给我的?祖母再也抑制不住悲伤,叫了一声“我儿!”便把父亲紧紧地搂在怀中。矮小的祖母,她只能搂到父亲的腰。父亲俯下身子帮祖母擦去眼泪,说,莫哭,莫哭,我好好的。我喝了七先生的“百沸汤”。七先生每天夜里都送“百沸汤”我喝。那“百沸汤”就跟灶头的扬尘水一样难喝。他还教我唱《庚子歌》。 六 母亲搀扶着父亲,围着那具棺材转。父亲看看这里,摸摸那里。转了三圈之后,父亲摇着头对母亲说,我睡不下。 祖父讲禁忌,又把两个房叔叫来,要把那具棺材吊回到回马楼上去。父亲不同意。父亲对祖父说,放下来一趟不容易,等我歇息两天身体健了,请木匠和漆匠来整修一下,你看这榫头都松动了,缝里要刮油石灰,墨汁也漆得不亮,要弄几瓶真正的油漆来漆才亮堂。父亲又来到棺材头前,一边比划着一边说,要请漆匠在这里写个金色的“寿”字。唉,可惜是个二十筒的,不过县里开了大会,好日子就要来了。大,等日子好些,我给你办个十六筒的。 父亲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饭桌上。虽然还是喝的菜粥,但全家人都觉得菜粥远比那肉丸子萝卜丝汤要好喝得多。 你说是七先生诊好了你的病?祖父在饭桌上问父亲。 是的。父亲说,每天半夜七先生都来陪我。七先生用竹篙把屋顶戳了一个洞,正对着我的脸。然后,他像猴子一样爬到屋后的樟树上去摇伸到屋顶上来的树枝,那些果子便顺着瓦沟从那个窟窿里滚下来,落到我的嘴里。七先生再给我喝“百沸汤”,然后又给我唱《庚子歌》。 这么说,七先生还活着。祖父自言自语地说。 七先生是中过举的人,要不是科考制度被废除,他肯定能中进士,弄不好中个状元榜眼或探花的也不为奇。七先生虽然书读得多,却并不乐意出世谋差,只在青竹溪边办了一所青竹书院,教孩子们读书。在民国的时候,金城镇的许多读书人都是他的学生,就连广济县城里的富人都把孩子送到青竹书院来。他的许多学生很有出息,有几个还在民国政府里做了大官。七先生是个很儒腐的人,在我们当地繁衍了很多的故事。 有一天,七先生走在田埂上,看见田里有一头壮硕的牯牛在耕田。七先生立即把那个年轻的农人叫上岸来,提起文明棍指着他的鼻子说,这条牛孕了崽你看不见吗?怎么还要它耕田?那农人连忙解释道,先生,这是一条牯牛。七先生却不容他分辨,大声地喝叱道,就算是条牯牛,这大的肚子,没孕两个至少也孕了一个吧?说完就挥舞着文明棍将那农人一顿暴打。 民国二十七年,日本人打汉口占了金城镇。七先生的一个学生在军队里做着大官。这个学生不忘师恩,派两个兵来把七先生接到汉口,然后又安排他坐飞机去重庆。飞机一起飞,七先生往舷窗外一望,看见这铁家伙不是在地上跑而是在天上飞,便操起文明棍去打他的学生,说,你做这种鬼事,让我坐这种无根无绊的“铁麻雀”,不是想摔死我?到了重庆,一钻出“铁麻雀”的肚子,七先生便扬长而去。他认定了那个学生是要害他,便一个人跋山涉水走了回来,从此再也不理他的学生。 他一生都是孤身一人。 解放后,政府不准办私学,七先生便失了业。七十多岁的人了,也不能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于是,他整天只在青竹溪上下游荡,有时几个月也见不到他的影子。慢慢地他便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大家都猜想,七先生肯定是走失了。再一推算,七先生当有八十多岁了,说不定是死在山上被野狗吃了也不足为奇。 八十多岁了,还能爬树?祖父问。 跟猴子一样,灵捷得很。父亲说,我明天去找他。 第二天一早,父亲便提着一只瓦罐过了青竹溪。瓦罐里是母亲给七先生熬的菜粥。按照头天夜里祖父和父亲的商量,由父亲到那幢废弃的屋里去等七先生,然后把七先生接回家来。 日出辰时的时候,父亲一跨过弃屋里那条青石的门坎,他手里的瓦罐便跌碎在那条门坎上,菜粥泼了一地。青的菜白的米两色分明。父亲看见赤身裸体的七先生仰躺在那张翻转的竹床上。他双手交叉搭在腹上,两眼微闭,只有那撮雪白的山羊胡子坚挺地指向苍穹。父亲扑通一声,屈膝跪在了七先生的面前。
七 我家的东墙头外,临时搭了一座草棚。七先生端坐在一把竹椅上。父亲按照“上五下七”的风俗把七先生的寿衣穿得整整齐齐。七先生的脸上覆了一张黄表纸。他的双脚被架在一块土砖上,那双寿鞋也是前几天母亲为父亲赶做的,圆口滚边,千层的布底。 那具二十筒的棺材仍然搁在两条长凳上,请来的漆匠正在用油石灰抿缝。父亲专门跑到金城镇上去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油漆,只好再到小学堂里去讨来两瓶墨汁,兑上桐油,漆在棺材上总算有了一点亮色。在棺材头上,父亲请漆匠用刷标语的广告色写了一个“福”字。 送七先生上山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也有些邻村和镇上的人闻讯而来。全村人斗了几斤米,在我家的大门口架起一口大锅熬了一锅菜粥,算是对“八仙”的犒劳和村外来客的招待。 七先生起身的时候,灵牌由父亲端在胸前。在“八仙”们的尖啸的呼叫声里,父亲唱起了那首《庚子歌》: 哟嗬——,哟嗬——, 叫我唱歌就唱歌哟, 我要唱就唱庚子歌。 鼠目寸光锁关国, 胆小如鼠抱头窜。 首鼠两端是妇人见, 鼠屎污羹坏了一锅。 哟嗬——,哟嗬嗬——, 时逢庚子有奇事, 庚子年里的苦难多。 甲兵百万是白纸扎, 不对那娇艳花一朵。 阴盛阳衰国就是家, 红毛绿眼八个妖魔。 哟嗬——,哟嗬嗬——, 人定胜天要大跃进, 风吹石磙怎过得江河? 家家米坛子都刮干净, 十粒大米煮了一锅。 弟弟吃了三蓝边碗, 还留三碗给哥哥。 哟嗬——,哟嗬——, 叫我唱歌就唱歌哟, 我要唱就唱庚子歌…… 北京治好白癜风要多少钱初期白癜风能不能治好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xw/4376.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当代汉诗原创龙红年一个人想钓上整个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