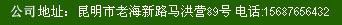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久居城区,就会深深地感受到城市中的嘈杂浮尘之苦。为了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我携妻子于四月中旬的一天来到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位于武功山北麓的蔡家村。很多很多年过去后的今天,这里除了新修水泥公路上奔驰着几辆摩托车和村中建有一些钢混结构、外墙贴上了白瓷砖的飞檐小楼外,从大的环境上看不出比从前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天空,依然是蔚蓝的底色上涂抹着几朵悠闲的白云。河流,依然是澄澈见底,一朵朵水花在河床中嬉闹着,小鱼儿在水中的石块下面悠游,羽毛上被点上了桃红色颜料的鸭子们一个劲儿地在河床中间扎猛子觅食。巍然耸立着的武功山吊马桩遥遥在望,俨然是一位坚守岗位的哨兵,虔诚地永不疲倦地守望着这一片绿色的家园。蔡家村的小街,静静地目送着每一次的日出日落、雨洒雨收,只是在我的眼瞳中,它比我孩童年代印象中的那一条小街似乎显得更窄一些更短一些了。 是的,这条小街上曾经留下过我数不清的足印。那时,墙脚下那一串串的黑蚂蚁,也曾是我和小伙伴们久久观察的对象……一个人的少儿时期不知道什么叫艰难,什么是忧愁,天真的心灵是他澄碧的湖泊,离奇的梦想就是他创造的故事。斗转星移,日月如梭。我表哥家屋侧的那些柚子树、椿树和屋后的那一大片樟树林子哪儿去了呢?那经常可以见到的樟林里的白鹭鸟儿们哪儿去了呢?我从前的那些小伙伴们又都哪儿去了呢?再过几十年,这条小街该不会不再存在了吧? (蔡家贞节牌坊旧照) 我独自一人信步走到村边的水泥长桥上。这桥从前是没有的,那时,这河面上只有一道石块砌成的拦河坝,人们要到河对岸那边去放牛、打柴什么的,便只有小心翼翼地踩着那些石头跨过河去。那些婶婶们大姨们,每天早餐后在这河边上抡起捣衣棒,一边捶打着要漂洗的衣物,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记得有一天这地方下了一场大雨,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蔡家村小学一名女生过河回家时被洪水冲跑了,她妈妈坐在这河的对岸捶胸放声号啕痛哭,河这边有很多人站在河边观看,老人们个个扼腕叹息,一些女人也悄悄地陪着那女孩的妈妈落泪。那天我姨妈也拉着我去了河边上,只见河中浑浊的洪水滔滔而下,一去再不回头。这一幕凄凄切切的情景,我一到这河边便从我的记忆深处冒了出来。 这河洲上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去玩耍的乐园。我们有时在河洲上用双手扒出一个个小池子,用碗盛些水进去,然后将我表姐从小水沟中用竹撩箕捞上来的小虾小鱼小螃蟹们放进小池里面,等到第二天,我们再跑去河边看那些小东西还活着没有。有时我们还在河洲上用石头“搭灶”,拾来大水冲来的枯树枝,或是割来一些枯茅草烧火,拿来家里的铁勺当锅使,炒南瓜子或是大豆,吃起来那真是香得很哪!这可是我和小伙伴们最愿意做的事情了。 看,一个身穿小迷彩服的小孩跑上桥来了。如今的这些孩子们,可不会再去玩我们童年时代那些玩意儿了,也不会再去玩“捉迷藏”、“跳飞机房子”那种古老的游戏了。时代在飞速进步,他们可以看彩电,放光碟,玩塑料手枪,弹小钢琴,等他们长到了八九岁,便能够在家中玩简单的电脑游戏了。现在的孩子们幸福得很,也比我们小时候聪明伶俐得多。 从蔡家屋场到苍老再到东江,其间有好几华里的路程。虽然现在我对这里的人大都感到陌生,但这里的环境我可是太熟悉了,可以说,它是烙印在我脑海里的一张永不褪色的地图。我离开蔡家姨妈家时只有七岁多一点,然而我后来上中学时,每学期的星期天中我都会来几次,直到我参加了工作以后才来得少了。这里有一种别地方所罕见的特色,地势比较平坦但石头特别多,几乎田野中的每一条田埂都是用石块垒成的。在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有一堵堵随处可见的石围墙,它不用水泥或是三合土填充石头之间的空隙,纯粹是用一个个光溜溜的石头垒起来的,这些石头墙大约有一米来高的样子。这些石围子里面不养鸡鸭,也不是用来圈羊,而是种蔬菜或是种水稻。这里的石头之多,令山外进来的客人感到惊异,触目即是。河床里也满是各种各样的石头,真可以说是一个石头之乡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与表姐去河洲上拾来那些白玉般半透明的石英石,拿在手上相互敲击,看那撞击产生的火花,然后拼命去嗅那带着一丝腊肉香的硝烟味儿。这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桐子树特别的多,这边几棵那边几棵,它们点缀在村前村后,河边墙角,显得疏朗有致。这些桐子树与石田埂石围子组合成一种独特的田园景观,散发出一种迷人的田园韵味。 桐子树有着阔大的树叶,那些树叶生长在树枝上面犹如堆翠叠绿一般,一阵风儿吹过,它们便都婷婷袅袅地舞动着身子,向路人展示自己的风采。每到桐子树开花的季节,这些白色的桐子树花好大好大一朵,真的是灿若云霞,几可与牡丹花争艳媲美,很是惹人喜爱。桐木是制琴的上乘材质,制琴巧匠用它制作出来的琴音色优美,据说即使是演奏者的琴技逊人一筹,如果他用桐木所制之琴演奏,也依旧动听。如果是一流琴师用它演奏曲子那就一定会产生沉鱼落雁的效果了,谁说不是呀?孔夫子他老先生在齐国听了韶乐,尚且“三月不知肉味”呢! 在我那遥远的记忆当中,蔡家小学操场的入口处有一座高高的四柱麻石牌坊,人们都把它叫做什么“贞节牌坊”,说是皇帝颁旨批准建的。然而究竟那座石牌坊是纪念谁的,是什么年代建的,当时究竟是官府出钱建的还是被纪念者本族祠堂出钱建的?我均一概不知。然而,那石牌坊精致的结构,那肃穆庄严的样子,多多少少总还是残留在我的记忆中。而后来,我估计应该是在“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运动期间,这座象征封建主义、摧残妇女青春的石牌坊,理所当然地受到“破四旧”运动的冲击,被人们拆掉了吧。谁来拆掉它的?谁指使他们拆掉的?到如今似乎都已成了一个谜。真的是太久太久了,记忆中总是恍恍忽忽、朦朦胧胧的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明朗,只是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 现实中,过去的一切都已消失,这消失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时代的进步吧。蔡家村还能引起人们想起过去的,是那黄土墙上,当年红军驻在这儿时用土红或石灰浆书写的大幅宣传标语。是的,当年红军战士、农会干部们冒着丢性命的危险闹革命时所憧憬的一切,现在全都实现了,而且应当说比当年人民群众所憧憬的还要好上好几十倍啊。当年那些穷苦人想过家里能放电视节目当“千里眼”吗?没有。想过人人身上揣着个手机当“千里耳”吗?当然也没有。当时人们所憧憬的,不过是耕者有其田,能吃上饱饭,不受人剥削和压迫而已。 麻田乡蔡家村的确很小很小,小到在江西省地图上都难得找到它;蔡家村也很大很大,大到我这一辈子都能够记住它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四十年前蔡家村小街上那段不长的石板路,永远在我心中延伸……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欣赏身边的风景了? 请儿童白癜风的饮食症状是怎样湖北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最新消息赣深高铁吉安到深圳预计最快2小
- 下一篇文章: 心系武大,情满珞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