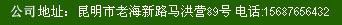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我的旧体诗小集 ——年9月至年6月于天台山 (第一首) 佛陇漫步 南北金银地,东西日月城; 朝行智者路,暮浴湛然风。 天台山智者塔院所在的那道山陇,因为诞生了中国佛教天台宗,而得名佛陇,乃是南北走向。其南端,原有圣僧定光禅师之茅庵,禅师在梦中曾向年少的智者大师招手。多年后,智者大师来到佛陇,见到了定光禅师,面对着周遭的一切,恍如故地重游。 当时,定光禅师告诉智者大师:“此山金地,老僧居之;北岭银地,汝宜居此,汝宜终此”。禅师一语成谶,后果如所言,智者大师得以留驻天台山,在银地岭下禅修。十方僧众闻风而来,渐成道场,名为修禅寺。 智者大师圆寂后,弟子们奉大师遗命,就在佛陇银地岭头,植松磊石,建成智者大师肉身塔院,安奉大师的不坏肉身。如今一千四百年已过,大师肉身早已因战乱而不知去向,但塔院仍在,仍保持着清末的基本建筑格局。塔院古朴而清幽,历来是高僧辈出的佛门圣地。 一九九九年九月,当天台山佛学院在智者塔院开学的时候,那是一个殊胜的因缘,每个人,无论是法师还是同学们,都感到了一种欢喜,一种身心的安乐与清凉。毫无疑问,这必定来自于祖师道场的无形加持,来自于祖师菩萨们的余德护佑。 我也一样,内心充满了欢喜与清凉。当我时常经行在佛陇之上,在定光禅师曾经居住过的金地岭头和塔院所在的银地岭头之间,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如此往复漫步之时,陪伴我的,是东山上生起、西山上落下的太阳和月亮,那重重的山峦,似乎就是日月的城堡与故乡。 脚下的路,那一块块儿黝黑的石头,是智者大师曾经走过的;而如此的出世修行之路,也必将是一切智者之归宿。佛陇之上,山风清爽湛然,而这天台宗教观双美之宗风,都源自于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即《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也都由唐代中兴天台宗的湛然大师所阐释与发扬光大。湛然大师晚年亦居于佛陇,并安葬于此。 每个早晨,每个傍晚,我就这样追随着无数历代高僧的脚步,漫步在佛陇之上。迎面吹来的是清凉的山风,也是智者大师和湛然大师等一切天台祖师们的清净道风。 一首小诗,一首五言绝句,对我来说,就是三年塔院生活的缩影,那是一段不可或缺的成长时光。 (第二首) 题某师行脚图 勘明世相已中年,淡去荣华好问禅; 昔日豪车频代步,今朝枯杖伴秋山。 不思尘欲心胸阔,才到无求天地宽; 水复山重何所适?菩提树下始心安。 曾与偶遇的某法师同游石梁山水,无意间得知,其乃富家子弟,曾有名车为伴。人到中年,历经了一些波折,幸好尚未成家,深感人世无常,于是遁入空门,潜心修行。 此法师衣着简朴,身形颀长,再加上手里握着一根竹杖,在石梁山水之中颇为入画。当时,借着夕阳金色的光辉,即兴拍了一张照片,胶片洗出来以后,效果很好,特意题诗一首以记之。 如今,此法师的大名早已记不得了,底片也已不知去向,唯有一首小诗,记录下了那刻心境交融的光辉。 (第三首) 朝天童寺宿奎焕楼 ——和王安石七言一首 小坐窗前心欲空,半楼细雨半楼风; 蓦然一记钟声到,恍然西天极乐宫。 二零零年五月,曾与佛学院全体师生一同参访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阿育王寺有幸礼拜并近距离瞻仰了佛陀的真身舍利,每个人所见的舍利子各不相同,我看到的是两粒灰白色,绿豆大小的舍利子,略微有些泛黄。 到了天童寺,先去拜见了方丈广修大和尚,大和尚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法师和学僧,非常欢喜,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客房。我们几位法师住在奎焕楼,别名御书房,建于康熙年间,过去一直是敬奉御赐佛像和书画的场所,近年则改用为上客房。 奎焕楼自成一个院落,虽然不大,却十分幽雅别致,名花佳木,错落纷呈。还记得,当时广老就坐在院子里的大藤椅上和大家侃侃而谈,一个劲儿地提醒我们,现在条件太好了,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大家一定要惜福,等等。 天童寺坐落在宁波市鄞县的太白山下,是晋代古刹,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为明、清两朝禅宗的重要道场,也被日本曹洞宗奉为祖庭。历来乃文人士大夫们所必游之胜地,也留下了不少诗词书画等作品。 当我在奎焕楼住下以后,无意中看到了王安石的一首诗,便随手抄了下来,诗曰: 山山桑拓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 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 回到房间,独自凭窗静坐。窗景当中映现出寺院里好几个殿堂的檐角,角端挂着铃铛,从近到远,高低错落,俨然一派古道仙风。说实在的,面对着这样的景象,令人凡心难起,杂念难生啊。 忽然间,一阵清风徐来,送来了窸窸窣窣的小雨,细密地飘落着,竟有几滴飞到了我的身上,一时间,正是风雨满楼。 在轻风细雨当中,四周显得格外寂静。远处的人声被风雨声完全掩藏了,只剩下一片纯粹的自然之音,一种怡然世外的空旷氛围。 就在这时,一记钟声凌空荡起,悠扬而来。那感觉,呵呵,仿佛此身早已不在娑婆世界,而是移居极乐国土了。于是,便有了这首小诗,借着王安石先生的韵脚,记下了那刻凭窗独坐的心怀。 (第四首) 驱车登佛陇峰 日暮苍山外,车行古道中; 方登真觉寺,又见夕阳红。 九九年十一月前后,一次外出归山,赶上了县城到石梁镇的末班车。班车驶出县城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一轮红日,恰在山峦之巅,并逐渐隐去了。 随后是十公里左右的上山路,当地的司机,本来就轻车熟路,看看天色不早,大概也急着回家吧,于是,在空无一车的山路上面飞驰起来。就那样在松林掩映之中盘旋着,简直有点儿坐过山车的感觉。 仅仅十来分钟,就到了佛陇山脚下,下车以后,独自沿着石阶攀援而上,呼吸着久违了数日的清新空气,脚步格外轻快。才到陇头,已经隐约可见竹林中寺院的石墙,忽然觉得背后有啥东西特别亮,回头一看,嗬!——竟是一轮完整的红日,再现于山峦之巅! 呵呵,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于是,我不由得驻足静观,目送着火红的日轮再次悄然隐去,方才踏着暮色回到智者塔院,又名真觉寺。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里面,观两度日落,对我来说,可谓是此生之奇景了。 (第五首) 中秋独坐 难得中秋月,相伴到凌晨; 一盏孤灯下,十年两样人。 昔时多顾虑,此刻少纠纷; 古寺松涛里,清风时可闻。 一九九九年的中秋,是我出家并受戒以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说来惭愧,我竟然在受戒后不到半年的时候,就被邀请做法师讲课,而且从来不曾读过佛学院,不曾接受过相应的佛法教育。毫无疑问,这是在佛教人才青黄不接的年代才会有的特例。 大约月真法师和无忧法师两位教务长看我是同龄人,接受过社会上的所谓高等教育,也是学佛好几年的居士身份出家,似乎还善于言辞的缘故吧。总之,我就这样充数到了法师的队伍里面。第一个学期讲《小止观》,也叫做《童蒙止观》,或者《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天台宗止观的入门读物,智者大师亲笔所著。 记得开学前二十天左右,当无忧法师把《小止观》的课本拿给我,问我是否有信心的时候,我随手翻了一下从未谋面的《小止观》,立即回答:“没问题。”——唉,谁让咱天生就不是谦虚的人呢。 当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参考着备课笔记,讲了四十五分钟,简要介绍了天台宗止观的特色与构成,所谓圆顿止观、渐次止观和不定止观,此三种止观,都以化法四教当中的圆教见解为基础,在开解的基础上而发起修行,依各人的不同根性,选择不同的止观修法,等等。 教务处的几位法师都参与了旁听,下来的评价是:具有三年教学经验的法师也不过如此。但我自己明白,咱是纯粹的教学相长,现学现卖。 在整整一个学期当中,本着教学相长的态度,我把《小止观》学习着讲解了一遍。佛学院的法师和同学们都比较满意,我自己也比较满意,因为尽力了,在学修上面也颇有收获。据我自己亲身体会,讲经说法当中受益最大的人,通常并不是听讲的学生们,而恰恰是讲课的人自己。谁会比讲课的人下的功夫更大呢?因此,也不会有人比他们收获更大。 不过,作为佛学院的办学出资方,国清寺的许多执事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纷纷议论:一年几十万的资金办学,目的在于培养僧才,你们竟然请刚刚受戒的人来做法师,这教学质量岂不形同儿戏? 对此,教务长月真法师心中有数,于是,当国清寺常住邀请佛学院的法师前往讲经的时候,便特意派遣我为代表,我则针对他们的水平现状,由于《金刚经》和《心经》已有法师讲过,便选择了《佛遗教经》,一部最入门却又特别重要的佛经。 讲经完毕,质疑者哑口无言,其他人一片赞叹之声。从此,整个天台山再也没有人质疑佛学院的教学质量了。乃至于,连一向对佛学院的办学方式不感冒的界诠法师和台湾的法藏法师,于二零零零年一起到智者塔院朝山的时候,对于当时天台山佛学院的道风和师生素质,都不由得脱口赞叹。界诠法师说的话,我大约还记得,意思是,他到过很多佛学院,不过天台山佛学院和其它佛学院不一样,有修行的气息。 说实话,天台山佛学院首届的几位授课法师,如:来华法师、一沤法师、一方法师和后来剃度的定智法师,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法师。虽然当时大家都只有三十来岁,都没有太多的教学经验,不过,大家的共同点便是有着端正的知见和纯粹的修行之心。 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几位法师还是法师,还在修行和学习当中,没有任何一人成为名利场当中的弄潮儿,尽管他们完全有这样的机会和资历。有这样一批道念纯正的法师们领众修学,天台山佛学院虽然是初办,也自然会具有与众不同的修行气息。 相应地,天台山佛学院的同学们也是人才辈出,其中最优秀的,当属允持法师、源宏法师和道泓法师,都成为后来佛学院继续办下去的骨干力量;而印恒法师则一直在闭关静修;传灯法师回到了家乡峨眉山之后,也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法师。 其他就不一一细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反倒是几位修学水平处于中下游的同学,因为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混得比较风光,有两位已经升座做了方丈,还有几位做了寺院当家,或者县级佛协会长之类的角色。 一九九九年的中秋佳节,当我独自静坐到凌晨,对月品茶,在将到而立之年的时候思维着自己小半生的经历。尤其是十年来的人生变迁,从一个踌躇满志而有些迷茫的普通大学生,到一个推销设备的公司职员,到一个居士,再到一个僧人,乃至于在受戒后,竟然添为一位法师。呵呵,如此过程,何异一梦呢! 将近而立之年,我无有可立的事业,只是树立了人生的方向。此生只愿与佛相伴,与法相伴,与一切清净僧相伴,与菩提心相伴,与出离心相伴,与解脱智慧相伴。而绝不愿与名利相伴,与虚伪追求相伴,或者,与那些无聊的杂事相伴,更不愿意与那些空虚的人们相伴。 我宁愿与虚空相伴,与日月的光明相伴,与原野相伴,与一切自然而自在的事物们相伴。若能与无为相伴,此生别无所求矣。 (第六首) 佛陇观晴空云海 霞似轻烟月似船,丹霞白雾景相连; 群峰杳杳朝台宿,涧水依依伴夏蝉。 闻香始忆高明寺,拭目难寻老城关; 万里白云生足下,怡然信步到天边。 佛陇峰海拔六百多米,不高,但在一年四季当中,每逢雨后却时常云雾缭绕,好一派佛国仙山。 二零零零年的夏秋之交,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天朦朦亮,一盏弯月还挂在天际,万里晴空当中,只在东方有几缕云霞,已经被尚未升起的朝阳映红了。脚下竟是一片苍茫的云海,把远处的一座座山峰,凭空烘托了出来。忽然联想到以往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峰曾经看到的一番景象,云海里,四周数不清的山峰,层层环绕,仿佛在向主峰朝拜一般。这一刻,大约也是如此吧。 坐落在佛陇峰东面山谷里的高明寺,在幽溪之畔,面向着佛陇而建,背后是重重青山翠柏,平日里,是我在佛陇漫步时的一道风景,此时,却早已不知去向。要不是寺院里的香烟淡淡地飘到了我的鼻端,几乎要把它忘却了。还有佛陇西南方的天台县城关,平时可以清晰地瞭望,此刻,也被掩藏在云海之中了。 那一望无际的漫漫云海,把佛陇峰雕成了一道狭长的脊梁,云雾的波涛,几乎就涌动在我的脚下。于此情此景当中漫步,真可谓心旷神怡,如在天际也。 (第七首) 幽溪 回转松坡下,美草覆春泥; 湿足知临水,闻声不见溪。 佛陇峰东侧的山谷里有一道隐秘的溪水,名为幽溪。明末的天台宗祖师幽溪传灯大师,就是以此溪为号。大师常住在高明讲寺,深入止观,宣讲法华,著书立说,有《净土生无生论》、《性善恶论》、《楞严圆通疏》和《天台山方外志》等等著作传世,为一代高德。 有一次,二零零零年的春天吧,我试图探寻一下,看看所谓的幽溪到底幽在何处。于是,手握竹杖,脚蹬罗汉鞋,沿着佛陇峰东侧的山坡回转而下,穿过了松树林,来到了坡底的草地上。时值春末,正是美草丰茂的季节,空气中到处洋溢着泥土的芳香。 有一阵子没下雨了,脚下并不泥泞,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以至于,不知不觉间鞋子和袜子都湿透了,才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溪水当中。于是,停下脚步仔细倾听,就从前方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然而,所谓的幽溪,依然了无踪影。 ——哈,真是幽溪呀!看起来是一片草地,其实呢,在草丛当中的沟沟坎坎里面,就并排流淌着十几条小溪呀。 (第八首) 雨后即景 千年老树生新绿,昨日花开今日红; 雨打风吹尘垢尽,平添山色几多重。 智者塔院外的竹林中有几株老樟树,看起来似乎已经半朽了,在一场晚春的山雨之后,终于冒出了些许嫩芽,焕发出了迟暮的生机。各色的小小野花们,在雨后显得格外鲜艳。经历了一场风吹雨打之后,空气变得特别净洁,平时看不清楚的远山,此刻,一层层地展现了出来,犹如水墨画一般。 这首小诗,有人曾问我其中有何寓意,我回答:诗歌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感觉罢了,未必有何寓意。 时常拥有一份美好的感觉,拥有一份超越的心境,所以就有了诗。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第九首) 古椴花开 椴花开复谢,碎落一坡金; 枝高少俗艳,幸能免入瓶。 天台山上有一种树,学名叫做“南京椴”,佛教界称之为“天台菩提”。所结的树籽,就是教内闻名的“天台菩提子”,用于制作佛珠,朴素而精巧,深得海内外信众的喜爱。 塔院周围颇多此树,每年农历的五月间开花,花色金黄,花形细小而清香,品位不俗,堪与桂花相媲美。由于天台菩提树形高大,顶端枝条比较细,几乎无法被人们采下来插在花瓶里欣赏,往往都能够得以善终。 当那些细小的花朵们开败了,纷纷谢落的时候,就会在林荫道上铺一层细密的金黄,如一张雅致的地毯,仍然散发出淡淡的余香。每到这时,散步的我都不忍信步踩踏,而是尽量从路旁绕过去,让默默的菩提花发扬出它们最后的美丽。 (第十首) 方广寺闻游客语偶拾 走罢唐诗路,临溪一盏茶; 客居石梁寺,自恨早成家。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适逢周末,佛学院没有课,便步行二十几里到石梁方广寺小住,一赏石桥飞瀑之美景。 碰到一位游客,从新昌沿着所谓的“唐诗之路”一路徒步而来,在方广寺暂住歇息。当大家一起坐在走廊里,面对着石梁飞瀑和澄澈的溪水,品味一盏清茶的时候,他很感慨,屡屡表示非常羡慕这样的生活,非常羡慕出家人。只可惜自己成家太早,如今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就是如此。“世人都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何止是功名,娇妻爱子,你我是非,种种爱恨纠缠,般般贪欲嗜好,等等,人们哪一样丢得下呢。 (第十一首) 山居偶感 独坐云边心自闲,山中岁月几多年; 菩提花落心经塔,又是人间五月天。 智者塔院的旁边,有一个闲置的小小院落,四周是竹林、松树和几株天台菩提。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吧,国清寺和日本天台宗共同在这里建立了一座“中日般若心经塔”,里面存放了两万份信众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用来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 次年初夏,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到智者大师说法台去观云雾。在路亭里面对着云涌雾绕的群山静坐了一会儿,境随心生,心随境显,眼前是淡淡的云雾,杳杳的山峦,令人忽有遗世忘年之感。 归来之时,走了另一条路,恰好经过“中日般若心经塔”。猛然发现,小小的院落里面,湿漉漉的石板上,竟铺满了夜落的菩提花,黄灿灿的,煞是好看。心经塔上也有很多,把小巧的塔身勾勒出了一个自然的轮廓,呵呵,好一个“菩提花落心经塔”呀! 于是,一种诗意自己蹦了出来。回到房间,略微梳理一下,就成了这首小诗,记录下了那个与云雾相伴,与菩提落花偶遇的早晨。 (第十二首) 雨中游济公院 南国五月青梅雨,十日阴阴半日晴; 欲向天台访道济,且凭风雨上赤城。 江南的梅雨季节,就浙江来说,大约发生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前后持续半个月,或者二十天左右不等。据说,之所以叫做“梅雨”,是因为正赶上了杨梅成熟的时节;另外,梅花的果实——青梅,也长大成形了。 梅雨通常是持续而细密的小雨,天色是阴阴的,却似乎看不到多少乌云,就是一片灰蒙蒙,雾沉沉,湿漉漉。一个星期当中,也难得遇到半个晴天。 大约是二零零一年的梅雨季节吧,我在小雨当中登上了赤城山。这座只有三百多米高的小山,由于拔地而起的缘故,看起来竟然格外壮观,山的形状似乎就像一座宽厚的天然宝塔。再加上红褐色的岩石,映衬在周围的青山绿水当中,尤为醒目,堪称天台山之地标。难怪,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大诗人们都对赤城山赞不绝口呢。 小小的赤城山,自古就是佛、道荟萃之地,位列道家十大洞天之六。在佛教来说,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建造了著名的梁妃塔。同时,这里也是道济禅师,即“济公活佛”早年读书的地方。 在中国佛教里面,最著名的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观音菩萨,另一位就是济公活佛了。凡是中国人,可谓无人不知。 作为当地历史上的最大名人,道济禅师少时曾在赤城山读书。近些年,那里建成了济公院,供信众永久朝拜与参观。 (第十三首) 古井水 去冬言水暖,今夏谓水寒; 不知古井水,冬夏总一般。 智者塔院的东院有一眼古井,水质甜美。每到冬天,打出水来总是温温的,一点儿都不冰手;夏天呢,却又分外清凉。 二零零一年盛夏,当我把井水打上来,感受着那份清凉的时候,忽然记起,就在去年冬天,井水曾经那样温暖。于是,一首小诗悄然诞生。 当然,严格说来,无论多深的井水,在冬天和夏天其水温都是不一样的。夏天水温高些,但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却感觉到了水的清凉;冬天水温低些,由于天气寒冷,人们却反而感觉到了水的温暖。 古老的井水,一任人们体验着温暖与清凉。 (第十四首) 山居夏夜 烹茶共享云和月,俯瞰人间万点灯; 风止蛙宁蝉寂后,归来窗下诵佛经。 二零零一年的暑假吧,大部分法师和同学们在放假后,都各自出发,有的去看望师父或父母,有的外出云游参学。塔院里,顿然寂静。 于是,我的生活就变成了品茶、观景,静坐、诵经。在一个月明云淡的傍晚,我独坐在阁楼之上,温茶自品,陪伴我的,只有明月清风和淡淡的云彩。盘坐略久,要起来活动一下,便趁着月色打开寺院的小门,来到陇头的视野开阔之处。远方,可以眺望到天台县城,正是一片万家灯火。 在佛陇上面走了一个来回,夜深了,清风忽止,蛙声与蝉鸣也渐渐歇息。回到房间后,尚无倦意,那就澄心静虑诵一卷经文吧。 (第十五首) 枫林叶落 只身漫步到枫林,午后时闻鸟雀音; 红叶落成新草绿,江南冬月美如春。 二零零零年的冬天,天台山的枫叶似乎格外美丽,哪怕只是路旁的一两株枫香树,都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 下霜了,到了枫叶最红艳的时节。一个午后,我望着红叶而行,和煦的阳光里,随处可以听到各种婉转的鸟鸣。不经意间,来到了几株枫树组成的小小枫林,地上铺满了半干的落叶,在阳光下分外红火,就那样随意地卷曲着,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绚烂。 在绚烂的落叶旁边,缝隙间,一棵棵小草青幽幽地露出了头。呵呵,对于我这个北方佬来说,这江南的冬月,真是美如春天呀。 (第十六首) 九月即景 金银双桂谢,塔院秋色虚; 竹畔石墙上,默开一簇菊。 智者塔院有两株古老的桂花树,一株金桂,一株银桂。其中,金桂的树龄大约有三百多年了,是塔院的知名景物之一。“塔院秋色”在当地的文人雅士心目中,从来都是一席美景。 每到农历的八月间,中秋前后,金银双桂便会在秋风里怒放,那甜美而清雅的香气,呵呵,顿然弥漫开来,浸润得人们心神爽朗,往返流连。 大约半个月以后,到了农历九月初,桂花谢了,塔院里似乎再也难觅秋色之痕。一天,当我在各个大小院落里周游,感受着这千年古寺的朴实无华。忽然在竹林之畔古老的石墙上,发现了一丛亮黄色的花朵——是野菊花,在墨绿乌黑的叶子们衬托之中,默默地开放了。 (第十七首) 石梁古道闻蛙鸣偶得 落石寻水迹,空谷觅知音; 一片蛙声里,何劳更弄琴。 二零零二年的初夏,天台山佛学院首届的同学们毕业了,我便在石梁方广寺小住。一天,独自走进了最偏僻的一条游步道,愈行愈深,已是了无人迹。 激荡的水流涌动在山涧之中,哗哗不绝的水声里,夹杂着偶尔的轰鸣。眼瞅着,一块石头从山崖上跌落了下来,落入了滔滔流水,转瞬间没了踪迹。甚至连一丝涟漪都不曾泛起,滔滔流水,仍自滔滔地向东流。 在这空旷无旁人的山谷,流水之声唯我自闻,除了鸟兽虫鱼之外,怕再没有别个知音了吧。 走出山涧,沿小路攀援而上。山坡上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块块儿不大的水田,上方广村已遥遥可见。走入田间小路,斜阳里,到处是一片欢快的蛙声,鼓噪着,争鸣着,淹没了其余的声响。 不远处的公路上开来一辆轿车,在观景亭旁停下,两位雅士走下车来,支好了一张桌子,开始抚琴轻吟。只不过,对我来说,那优雅的琴声几不可闻,耳畔只是一片交响乐般的蛙鸣,洋溢着阵阵欢快。 (第十八首) 天柱峰访一沤法师 金溪流水杜鹃花,碧玉葱茏云雾茶; 山路蜿蜒行不尽,一棚茅舍在天涯。 一沤法师在华顶的天柱峰有一座茅棚,每周当中,没课的那几天,一沤法师就会到茅棚小住静修,寒暑假更是如此。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某个周末,约了两位法师,准备步行三十多里上华顶,前往茅棚参观,午饭后再原路返回。 那天大清早,吃过早饭就出发了。一路缓缓上坡,快到龙皇堂镇附近的时候,海拨应该有八百多米了。路旁的溪水格外清澈,在清早阳光的照耀下,泛出金色的光辉。正是阳春三月,溪水之畔,一丛丛杜鹃花(山丹丹)已悄然绽放。 顺着山路右转,开始向东面的华顶峰行进。上午十点多,到达了海拔一千米左右的葛玄茶圃,那是一座著名的茶园,一片碧玉葱茏,四季云雾缭绕,盛产最优质的天台山云雾茶。 从华顶主峰再转向东南方向,一条蜿蜒不绝的隐秘小路通往天柱峰,这里已堪称人迹罕至了。虽然只有几里,但一路上的感觉,却是几度峰回路转,茅棚之所在,似乎依旧万水千山。 终于,最后一次右转过来,眼前豁然开朗。与雄伟的天柱峰遥遥相对,我们的右上方出现了一间茅舍,周围满是苍松翠柏、野草山花,好一处人间净地,好一处世外桃源呀。 (后记) 塔院来了几位文化达人 大约在二零零一年的春夏之交,智者塔院先后来了几位文化界人士。当时由于我的十来首旧体诗写在了黑板报上,题为《超然法师诗选》,便引起了他们的宁夏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石家庄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哪家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99武义人不知道的隐世游玩地,去了还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