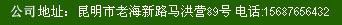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上个月与孝感的作家唐唐、冯致一起下乡采访,村道回环,乡塆错综,虽曰故乡,已成迷宫。掩映迷宫最醒目的树,其惟枫杨乎?枫杨粗枝大叶,翅果累累,浓密高拔,巨伞一般,将处处亦新亦旧,宛如大地深处长出来的乡屋拢入怀里。唐唐说这树是杨树,老冯说是“鸭娃树”,尚不知道它有这个风雅的学名。其实也不奇怪,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于祖父母、叔伯姨舅,这些熟悉的亲戚的大名,多半也是陌生的。枫杨与青杨、白杨诸北方迁来的威猛兄弟比较,身材也并不输给它们,喜水,向阳,春夏之交,又不会飞散令人烦恼的白絮。所谓“鸭娃”,大概就是指它们代替絮籽传宗接代的翅果,捋下来放在手掌上,堪堪就像小鸭子的扁嘴,明黄可爱。孟夏草木长,枫杨结成的果串,密集如同孟良焦赞他们的虬髯,又好像始皇帝冠冕上的流苏摇摇摆摆。我总觉得,它们子息绵绵的样子,大概是很能由乡下人那里讨到彩头的,所以挑剔的农夫们,才会留下这样又不能打桌椅,又不能做板凳,匠石掉头不顾的无用树,在陂塘边,宅基旁,肆意生长起来,由一指,一握,到一抱,长成几个孩子手拉手都围不住的一个老树精。蔽屋荫牛拱猪坐狗之余,它还供喜鹊与麻雀筑巢,随后金龟子、天牛、椿象和鸣蝉聚居在它的枝干上,蚂蚁军来来往往,蝴蝶族毛乎乎的幼虫彬彬有礼地蠕动,大头癞蛤蟆泛着白浆缓步树下,红绿蚯蚓黏黏地穿行在根须间……一棵成年枫杨,树大招风。这个“风”字,大概还有繁体“風”字的本意,说明枫杨能藏鸟纳虫,就是一个小小生物的王国。之所以跟“枫树”成了表亲,大概是因为枫杨的翅果,跟枫树的果实长相差不多。只是枫树鸭掌一般的叶子,十一月会被秋色染得深红,而枫杨粗眉大眼一般的对叶则渐变为黄褐色,去与秋雨织成“雨中黄叶树”的景象。说到表亲,大概还要加上槭树,槭树被称为“元宝树”,也是因为它的枝杈里会伸出一条条淡绿色的翅果。爱德华?威尔逊在《缤纷的生命》里,谈生物的多样性,适应辐射,又讲到“趋同进化”,枫树、枫杨、槭树大概就是一个例子,它们虽然呆在不同的科属里,但都修行出了带翅膀的果子。在湖沼里漂浮的蜻蜓幼虫,在泥土里蛰伏经年的蝉猴子,还有为自己身份而苦恼的蝙蝠,它们何尝也不是跟飞鸟,跟人类的飞机一样,在不同的区间里,达成了飞行的梦?凭借风的力量,乘着梦想的翅膀,是为了更远地离开家乡。童年时,春夏在枫杨树阴里玩耍,用“鸭娃果”拼图,非驴非马,秋冬躲在棉被里,倾听北风呼啸在枫杨的树冠上,我心里想,枫杨跟白杨、法桐、樟树、水杉、木樨不一样,它大概就是我家乡十里八乡的土产。成年后我有机会差旅各地,车窗里远眺,行走中抬头,好多次都认出了它熟悉的身影,才明白,风吹拂着它们的翅果,已经将它们带到了不同的远方。我曾在安徽九华山下的山谷里,看到过一棵“枫杨王”,它有一千多年的树龄,树身苍黑,像卧在溪水中的一头水牛。我还记得南京师范大学对面宁海路上姿态各异的大枫杨,作为城市中的行道树,它从容大方的样子,一点都不比法国梧桐差。有一次,我住在杭州郊外的民宿里,民宿白墙黑瓦掩映在七八棵高大的枫杨里。我由贵州的梵净山下来,路过一条布满五彩鹅卵石的小溪,溪边长满了数百年以上的老枫杨。我求学苏州,在拙政园里,就看到过陈从周老先生表彰的枫杨,苏童是苏州人,他写“枫杨村的故事”,多半也是像我这样,自小就中了枫杨的“毒”。如果将这些枫杨都标到地图上,由浙江江苏,到江西安徽,再到湖南湖北,大概就是江南、江淮、江汉与西南地方?北纬三十度上下,湿润多雨的山泽与池沼,亿万枫杨的翅果在由夷变夏的南中国发育成大树。要是两千多年前的楚灵王楚平王他们看到我目测的这个枫杨地图,一定会得意地讲,这就是寡人治理的楚国,但他们未必愿意将这种平常如水牛,如水稻的树封赏成“国树”吧。屈原写香草美人,未及给枫杨写出骚辞,倒是橘子树运气不错,他在《橘颂》里写:“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枫杨未必不嘉,也一心一意服役在南国,纷其可喜的,是绿叶与翅果罢了。一定要给枫杨写诗的话,陶渊明也许更合适吧!枫杨朴茂自然,多像他的诗风!他诗里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他在生命的暮年,听到过风吹白杨稠叶的萧瑟之声,也会跟唐唐、老冯和我一样,在少年与青年的时代,听到过风吹环绕我们村庄的枫杨国的声音:南风簌簌似蚕啮,北风忽忽如虎狂。 赞赏 人赞赏 中科医院专家北京中科医院曝光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xx/5021.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听老树讲故事
- 下一篇文章: 江西人为什么叫老表,这也许是最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