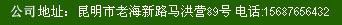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一、刚与柔:哲东的思想性格 樊健军的长篇小说《桃花痒》,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哲东的库区移民,他的性格在小说第一页就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哲东嫌她碍手碍脚,一脚踢飞了一只酒瓶。酒瓶的溜溜滚着,碰着别的酒瓶哐当哐当响,碰着的酒瓶又撞上了另外的酒瓶,满屋子都是酒瓶相互碰撞的声音,他喜欢喝酒,腰带上常挂着布袋子,袋子里装着瓶酒。他的那一脚很有威慑力,九兰和我躲到了一边,在他眼里她不过是只大酒瓶,随时都有可能飞起来。”这是一段小说味十足的文字,形象、幽默,哲东粗鲁、暴躁、嗜酒的性格跃然纸上。 哲东性情粗暴,像一头发情的公牛,但又粗中有细,心机深沉,小说对此展开了精彩的描绘。哲东一到水门村,就张罗着“拜码头”,给村中大佬送礼。他对送礼的对象进行了慎重的选择:太叔公明西是宗族的领头羊,村主任昆生是水门村的最高行政领导,小学校长海波和赤脚医生杏林关乎家人的教育与医疗,而高贵是水门村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掌握者”。在送礼时间的安排上,哲东也颇费思量:看望太叔公明西选择半上午,去昆生处送礼则安排“在晚上,上半夜,村里的人将睡而未睡之时”。小说于此处有一精彩的细节描写:“他带了手电筒,又不摁亮它,好几次我都撞到他的屁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哲东忍辱负重、老谋深算的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吩咐我写日记记录水门村心脏的情况,暗地告状扳倒昆生,安排小高贵当治安员兼民兵连长,等等。在哲东粗野、狂暴的外表下,是他的阴鸷沉静、心计渊深,他就像一匹从旷野里漂泊而来的狼,潜伏在水门村的暗角里。他就是水门村的勾践。 勤劳、务实、肯干、上进,他片刻也不得停歇。“对于筲箕窝的改造,哲东从搬过来的第三天就开始了,他扛着锄头,挑着土箕,在那片旱地上热火朝天干上了。”“当上十八组的组长后,哲东像被狗咬了,变得神经兮兮的,有点像孙猴子,不知弼马温是多大的官。他制定了时间表,早晨六点半起床出早工,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准时出上午工,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二点出下午工,七点收工,八点晚饭,十点钟睡觉。”他头脑灵活、目光前卫,能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脉博,他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语)哲东的身上有股顽强的“韧”劲,血液里流淌着“强悍”的基因。他因插秧未按方格而遭到“游村”的处罚,“他敲着铜锣,脖子上挂着纸板,就像个耍把戏的,”在孩子和群狗的押解下哐当走过。这对于哲东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但游村之后“他依旧斗志昂扬,每天清晨,三声哨响过后,他就在门前的场地上叫喊,十八组的,下地锄草。”正因为这股“韧”劲,他才在一次次被打倒后又重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挺得更直,站得更高,活得更好,直至最后一次被打倒。哲东是强悍的,他一一击败了他同时代的对手。有一回他竟然借黄毛来教训孝朵,他说:“做人就要像黄司令一样,别动不动就哭鼻子”。 他在家庭中是个暴君,对待妻子、儿女态度蛮横;他嗜酒、与米儿等女人偷情;他没有培养好孩子,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对九兰不忠诚,也不是个好丈夫。在他的身上,还保留着浓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他带我去太叔公明西那儿送礼,我想拉上孝朵,哲东说:“她是女孩子,将来拜祭祖堂都没她的份”。可以说,哲东这个形象是非常真实、饱满、有血有肉的,他不同于以往任何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如果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哲东正是属于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的人物,这是《桃花痒》的独创和贡献。 在这里,就哲东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性而言,我们还可以拿他同另一部著名小说《白鹿原》中的主人公白嘉轩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思想性格是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的,那就是“正”,他是“正统”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用时髦的话讲,他的行为总是传递着正能量。而哲东的思想性格则可谓亦正亦邪,但以“正”为主,“正”是主流、“邪”是支流、末流。从他身上的“邪”的一面既可看出人性的一般弱点,也可看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消极的一面,糟粕的一面,如成者为王败者寇,遇事只问结果不讲过程,讲手段不讲原则等等。但是,哲东身上虽然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忍辱负重、不屈不挠、顽强向上依然是他思想的内核、人格的本质,这令人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古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化和缩影。他的精神气质、性格内涵与白嘉轩有大不同,但亦有大相同,有共通之处。 二、浮与沉:水门村的“战争” 哲东一家融入水门村的过程是痛苦而艰辛的,哲东就如一颗棱角粗砺的砂粒闯入到了水门村这个蚌贝内,让水门村感到不适和不安。反之,水门村对这颗砂粒进行了巨大的挤压和吞噬,几乎两败俱伤。如一开始把哲东限制在簸箕窝不让其进入水门村的心脏,让哲东打锣游村,栽赃诬陷哲东为贼,过年舞龙灯不进哲东的堂前;当镇领导要在水门村召开“蟠桃会”时,一夜之间哲东的桃子却惨遭浩劫;被人打断三根肋骨,羊群也遭受袭击,就连“我”和孝朵都受到猪屁股、胖头他们的欺负……哲东来到水门村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 对哲东来说,他们本可以同樟树村民一起迁往“土坝下游”,但他没有,唯独他们选择了水门村。因为“水门那地方的人都姓樊。天下姓樊的人都是同一个祖先,都是兄弟姐妹。”哲东投奔水门村是去认祖归宗、是去寻找“组织”,是去“寻根”了。但水门村并没有敞开它应有的胸怀,他们没有派人去樟树村迎接哲东这个“四房”的兄弟,而在水门村接待哲东一家到来的“破絮”被证明是个贼,第一次见面就偷了哲东的粮食。水门村就是这样算计他、挤兑他,甚至把他当“入侵者”来看待,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排外心理。排外心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人性弱点,可以说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各个角落。人类为什么会具有排外心理,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问题,但究其原因,可能与人类进化有关。在人类茹毛饮血、食不裹腹的时代,外来者可能会抢夺自己的食物、带来生命的威胁,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因此,对外来者的警惕和敌视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水门村就成了宣泄这样一种本能的试验场,成了演绎那波谲云诡的人性的舞台,成了哲东的“狼窝”和“虎口”。 哲东,不容易。 面对以昆生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围追堵截”,哲东这匹来自异乡的狼渐渐地露出了他的“牙齿”,展示了他的“侵略性”:他一方面种桃树、养山羊,带领村民致富,让自己成了镇上、县里的典型,逐渐获得水门村民的爱戴和拥护;一方面他一步步把钢宝爹、昆生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并拉拢小高贵,分化、瓦解水门村的敌对势力。他冉冉初升,变为水门村蓬勃的太阳,而昆生则成了孤悬天边的那钩残月。而最后,他又败在了以“孝男”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手中,兴衰轮替,大浪淘沙,在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背后是那一只历史的和必然的翻云覆雨手,几多感慨,欲说还休,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 在哲东同水门村的系列攻防转换中,“圈套”这一章是小说情节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整个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如果说,之前水门村村民在反对哲东的行动中基本上是以一个整体面目出现,扮演着昆生的“喽啰”的角色,作为个体则形象模糊,那么在这一章中,水门村开始出现分裂——有的人追随哲东要种桃树,有的则坚决抵制种桃树——水门村的村民开始“觉醒”,人物的个性得以呈现。水门村的主要矛盾也已经由水门村同“外乡佬”之间的“内外”矛盾转变成为进步力量与落后势力之间的矛盾、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后来昆生设诈故意安排哲东填埋烂泥塘时,有的村民便暗中相助、执意不让昆生的阴谋得逞,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暖色。这样,小说中的“村民”形象逐步走向独立和丰富,因而也更见具体和真实,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对哲东实施钳制、堵截的力量中,大、小高贵是一个特例。他们是昆生的马前卒,扮演昆生“打手”的角色,带有黑势力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间,常常能看到这些“大小高贵”们,他们横行乡里,恃强作恶,但他们又不同于城市的黑社会,一般处于自发状态,无组织,大法不犯而小恶不断。由于乡间法制力量的薄弱或缺席,善良的乡亲门无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欲同他们斗争则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乡民们最后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乡土社会的这一现象。 作家铁凝曾说过:写短篇小说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情景,写中篇时想到的是故事,写长篇时想到的是命运。《桃花痒》的叙述时间跨度达三十余年,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前后水门村的社会历史变迁和移民们这一特殊群体艰辛困蹇的命运,作品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读者惊叹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表现力量,有的作品甚至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就在于小说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人物的思维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都是来自历史的现实,即令是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都不能例外,它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烛照着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从《桃花痒》中我们可以读出“变迁”是多么的不容易。 哲东的迁徙是被迫的。如果不是因为修建水库,我想哲东一定会留在樟树村过着那种“薯丝饭、茶壳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自满自足的生活,而不愿意来到水门村“热脸去凑冷屁股”,受着种种的“磨难”。中华民族恋乡守土、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的。但是,尽管哲东的“改变”是被动的,可他勇敢地接受了这种“改变”。站在今天现实的角度上,我们欢呼变革的力量,我们向变革者致敬! 三、虚与实:作品的艺术成就 虚实相生是一切艺术所追求的大境界。实是大地,虚是天空。实是山峦,虚是云彩。实是湖水,虚是波纹。没有实,虚成为空幻;没有虚,实走向僵死。《桃花痒》一方面细致描摹,让读者体会到小说之“小”,真切感受到移民创业生活的曲折与艰难:吃喝拉撒、每一个琐碎日子的甜酸苦辣;一方面又带给读者广泛的思考,让读者联想到历史、农民、土地、家族、变革这些宏大的命题,给读者制造了广大的审美空间、哲思空间和文化空间。《桃花痒》无限逼近虚实相生这一艺术的大境界。 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哲东、昆生等主要人物形象。按照小说的经典观点,人物无疑是最重要的。除了主要人物外,在此还想说说九兰和翠翠。 作者对九兰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却精彩传神。上文所引用的对哲东的描写,也包含着对九兰的描写。乍一看去,九兰是一个逆来顺受甚至是有点懦弱可欺的女人,就是在哲东事业红红火火同时与米儿也正缠缠绵绵、干柴烈火之时,九兰除了在家里骂几句“死鬼”之外,也不见她有太多的动静。而等到到了小说的结尾,哲东落魄之时——这里真是小说的精彩之处——九兰对哲东说:“来,我陪你喝两杯。”抱起酒坛,给两只海碗汩汩满上了酒。捞起一只羊腿塞给哲东,哲东接了羊腿,却不喝酒。九兰不理会他,端起另一只海碗,咕噜咕噜,把酒干了个底朝天……九兰说,酒有的是,羊肉有的是,你尽管吃,尽管喝。爷们得有爷们的吃相,爷们得有爷们的喝相,别死不拉叽,一个瘟相。这桌酒从午后喝到落日黄昏,月上柳梢,酒香四溢,羊骨头撒了一地。”在“我”因不愿意接受九兰安排的婚事而准备离家出走时,九兰(对我)说:“你要是敢出走,娘就死给你看。她把菜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菜刀寒光闪闪。”“菜刀抵住了她瘦弱的脖子,有血从刀口下渗出来。”一个隐忍、深情、善良而又性格豪爽、果敢、刚烈的女子形象在作者的笔下像雕塑一样矗立起来。她就是燃烧的烈酒,她就是仁慈的大地。而对翠翠,作者主要从“我”的视角去写她,用“虚笔”去写她,透出一种诗意的美,任凭读者去放纵自己的想象力。 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中的“我”刚出场时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在水门村一直成长到三十余岁,结婚成家。正如在前文所述,在哲东所扮演的角色中,作为父亲是最失败的,孝朵嫁给一个患病的男人,孝强离家出走,“我”则畏畏缩缩,把青春的梦想和美好握成了一根鞭子,在水门村的一个山旮旯里放牧羊群。由于哲东的粗暴,“我”畏惧他,甚至是仇恨他,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发誓从此以后不叫他爹,而叫哲东、哲东、疯子哲东、酒鬼哲东。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同“哲东”保持了足够的心理距离,因而能让“我”以中性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哲东的一言一行和水门村世相百态,保证了叙述的客观与冷静,这正是小说所需要的。 小说的语言纯粹、精致而流畅,虽为长篇巨制,读起来却无半点滞涩延宕之感,这反映了作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描写,甚至可以说是描写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这些描写绝大部分是写实的,但在很多段落中又有写意的风格,增添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如小说第十章《粉红》的第一段: 三年后的春天,下了一场粉红的雪,筲簸箕窝彻底被覆盖了。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一层压着一层,一树胜过一树。那些桃树长出了无数的手臂,相互搂抱着,手拉着手,织成铺天盖地的网,网眼里漏出的都是桃花,走在桃树下哲东的身体是红色的,脸是粉色的,眼睛是粉色的,腰间晃荡的酒瓶也是粉色的。 小说中这些大量的或实或虚的描写令我想到了莫言的代表作品《生死疲劳》,《生死疲劳》也可以说是由描写构成的。从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我并不喜欢《生死疲劳》的语言风格,我更喜欢那种蕴藉一点的、舒缓一点的、留白多一点的语言,但莫言《生死疲劳》的语言风格是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式的、是浓墨重彩斑驳陆离的、是涂脂抹粉性感明艳的,它就像一个口齿伶俐的女人,你未说出一句,她已答上十句,虽然你不一定喜欢她,但你又不得不佩服她火一样的才情和井喷一般的旺盛创造力。《桃花痒》的语言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每一处都写得很饱满、富于激情、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好似作者的全部才情和精力都要倾注在每一个词语中以让它跳动起来、奔跑起来。譬如小说第十八章《哑剧》写我的梦中情人“翠翠”送桃子给我: 为感谢我的帮忙,翠翠送来了桃子,桃子不在她的嘴上,而是放在背篓里。一共有四颗,每一颗都鲜艳粉嫩,让人馋涎欲滴。一口咬下去,桃汁立刻在口腔里跑开了,泥鳅一样溜来溜去,在舌头上尖叫,玩疯了闹够了,再一头钻进食道,冲进我的身体深处。他们不再是桃汁,而是变成了凶猛的火焰,一口一口啃噬着我的身体。我的肠子没了,胃化了,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水,滚烫的水,泛滥的水,将我的身体淹没了。我的身体像是只气球,膨胀,再膨胀,到了极限,快要炸开了。我死死裹住了自己的身子,掐住它,让它冷却下来。 写作时文思泉涌、下笔如飞,这正是作家所追求的绝佳创作状态,但是,若过于亢奋,也容易出现“用力太过”的毛病,但《桃花痒》并没有放任自己的激情,字里行间显示出谦卑和节制,这体现了作家艺术上的成熟。 《桃花痒》当然也存在着它的局限性,但更需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抱负和雄心。在此,笔者摘用评论家雷达先生当年评论《白鹿原》的一段文字于后,读者自可品出个中三昧: 若仅就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它不可能逃出许多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已经提供的范式。白鹿原是一片地域,黄土高原上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塬,散落着几个村庄。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两姓组成,形成一个大宗族,一个典型的基层文化单元,一个血缘共同体组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它具有初级性和稳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广大社会,内涵可以是广大社会的缩影”。于是,《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事实上,《红楼梦》、《静静的顿河》、《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从大的结构框架来说,莫不如此。我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芙蓉镇》、《古船》等,也概莫能外。 ? 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好北京哪些医院白癜风好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angshuzx.com/zszx/4386.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一个没有牵手的故事小说连载十六
- 下一篇文章: 艾尚影吧最新推荐暴力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