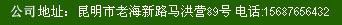|
文 南希姐姐 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大樟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立在村口。 你总跟外乡人说,樟树下,就是我家。 在中国,很多村口都有这样一棵粗壮的大树。 但如今,不少都市人都有块心病——故土远离,欲归无门。随着二三十年来城镇化的进程,随着祖父辈亲人的逐一离世,心理上和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似乎都已经回不去了。故乡的影子渐渐模糊,故乡的样貌形同陌路。 如此算来,我是幸福的。 我的故乡,仍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不离,难弃。 村口的大樟树,见证着村庄的来来往往 我出生的地方:“五角星”村诊所 我的故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很多县城都叫“城关镇”,小小的宁海县城也是如此。而我家所在的小村庄,翻过一座白峤山就到县城东门了,美其名曰“城郊乡白峤村”。 这里,曾是古宁海的县治所在。宋储国秀《宁海县赋并序》有:“以吴越为蛮索,春秋之所同贬,以台明为环富,词人之深羡。唯晋太康吾邑始显,截回浦而置郡,析章安而为县。初宅白峤,星霜岁远,旋徙海游,规模日浅。”意思是我县建县初期,县治为白峤。据宋《嘉定赤城志》载:“白峤山,在县城东五里。下有岭焉,晋武帝置县于此,今或于沙啧中得断壁甓云。”《崇祯宁海县志》也记载“白峤山,东五里,晋武帝初置县于此。” 当然,关于这些历史,是在我上学以后才逐步了解的,幼年的我并不知晓。后来我猜测,可能因为下白峤村有一个很好的港口,可以连接到东海,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才在此设县治吧。 我与这个村庄最早的联系,是作为婴儿,最初发出的三声响亮啼哭。35年前,我在村卫生所出生。我医院,因为墙上刻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显示了它的建造年代。 孩子们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年代的烙印 从我两三岁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幸福的身世。我是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前最后的时机出来的。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出生后,我家一儿一女,足矣,而且,刚好符合政策。更让人骄傲的是,那一年,我们村准备实行包产到户,16岁入党并早就是生产队长的父亲,在9月的一天,带人出去落实分田的事。可没走出多远,就有人气喘吁吁地赶来找我父亲,说我妈肚子疼可能要生了,让他赶紧去卫生所。在我呱呱坠地之后,父亲在那天下午继续带队工作,至此,作为新生人口的我,在红线划分的一刻,也分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分田地。所以,人们都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孩子。 我的奶奶、外婆和小伙伴们 此后的五年,我在村里幸福地被散养着。 每天早晨,父母带着哥哥,去田地里勤劳地工作,他们种植庄稼和果树。我几乎每天睡到太阳晒到屁股上,然后慵懒地独自下楼。奶奶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奶奶身体不好,我从来不烦扰她。院子里出来暖暖的太阳的时候,我会自己在阳光下洗头。奶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比如,她只吃鱼头和鱼尾,她说她就喜欢吃这两部分(这是一个很多中国孩子都体验过的老梗吧,但的确是真实的)。我会告诉她,我也喜欢吃鱼头,因为吃鱼头是做头领,可以当领导。 说起当领导,其实,我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什么小伙伴,因为我不知为何,总看不上那些小屁孩;而他们,好多人,也怕我。比如,我堂叔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姐,人称“雌老虎”。比我哥小一岁,比我大一岁。我哥经常被她欺负,但那女孩碰到我,却不敢吱声。胖乎乎的我,一板起脸,气势上就胜出了一大截(这算自带威严么?)。若要舌战,我更是能搬出一堆大道理来坏走那些“纸老虎”。大概我属于脾气特好,但一发脾气没人斗得过的主。 不仅从小表现出慵懒的气质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还早早地成为一枚正宗的吃货。这与奶奶、外婆甚至邻居婆婆们的宠溺不无关系。 这个小村庄盛产杨梅,“白峤杨梅”是宁海一绝。杨梅季节,除了在山上攀爬在树上直接囫囵吞梅(老人们总说杨梅核可以下肚,还能治拉肚子)。在家时,奶奶总爱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长线,把杨梅肉剔下来再给我吃,怕我吃太多“牙齿死掉”。 四岁的那年冬天,奶奶让我和哥哥去小店买盐。肥嘟嘟的我,因为贪吃屋檐地下晶莹剔透的冰凌珠子,不小心滑了一跤。结果,我们刚买回来的盐全撒了。情急之中,哥哥让我把白雪装进袋子里,带回家冒充盐给奶奶用。奶奶发现后,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笑得合不拢嘴了。 关于我,在这个村子里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五岁不到的我,到邻居家偷吃杨梅酒(实际上我记得是邻居婆婆喂我的嘛,因我父亲很早就让我用筷子蘸着喝酒),喝了一大碗,结果醉得呼呼去也。顺便提一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篇《我爱家乡的杨梅》就在《小主人报》组织的华东地区作文大赛上获得了奖项,所以说,从小没有白吃啊。 更幸福的是,我外婆家也在这里。我奶奶家是上街头,外婆家是在上街头和下街头的中间。要去外婆家得过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应该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拱桥,桥头的古树年纪也特别特别大了。每次外婆家磨豆腐,我都要去观摩,这一天,我会很早起来。一大清早,外婆就在大土灶上磨着热气腾腾的豆浆,最上面挂起的一层飘香豆腐皮总是归我的,因为听说那一层豆腐衣营养最好。晨曦照在外婆瘦小的身躯上,和灶头上雾气一起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剪影。 去外婆家必经的石桥 舌尖上的乡愁:麻糍,年糕和麦苗 如果要继续谈舌尖上的故乡,那些幸福往事,估计好几天都数不完。和故乡的难舍难离,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童年味蕾的记忆。在我们这个小村庄,不同的时节,要吃不同的美食。 比如,腊月的时候,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舂年糕(土话叫捣年糕),通常是两三户人家合捣一缸。在那种石头的舂里,把煮熟的糯米和粳米放在一起,用石锤不停地捣。寒冬十二月的夜里,温度那些低,孩子们在灶头下火堆旁搓着双手,眼睛则巴望着第一轮捣好的年糕。那一条条香甜软糯Q弹的年糕,吃在嘴里,暖在胃里,整颗心都要被融化了。 到了清明节,妈妈们则会带上孩子们一起到山间田野摘一种名叫“青”的小小野草(以前一直以为是艾草,今年才知道其实是屠呦呦获奖提炼青蒿素的青蒿)和野外松树林上的松花粉,利用糯米来捣清明麻糍,同样在现场吃热的是最美味的。清明的时候,除了漫山遍野的各色杜鹃花(花蕊可直接吮吸汁水,清甜味),走过一条条小河,河畔总有一些红绿色的小果子,那是“只只梅”,真的可以让人望梅止渴,哪怕多年以后再想起那小果子,都会口舌生津。清明前,家家户户都要舂“青麻糍” 五月的时候,初夏,可以上山采摘野草莓,我们叫它“麦苗”(实际是野生覆盆子的一种),清甜可口。同时我们一早就知道,有一种红白色的“蛇苗”有毒,绝对不可以摘来吃。到了秋季,山上的树丛里会长出很多紫色的野果,那叫“乌饭”(我哥说那是野生蓝莓),甜甜的口感让人陶醉。吃完以后满嘴的深紫色,则让同行的伙伴们忍俊不禁。这种果实,也是制作乌饭麻糍的主要原料。 故土难离:三十年后再回归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的思绪总是停不下来。想来的确是太幸福了。奇妙的是,兜兜转转三十年,在离开这个小村庄25年之后,也就是五年前,机缘巧合之下,父亲从县城的生意中抽身出来,承包了村口的一座小土山,亲自栽种了数百棵杨梅和白枇杷树,当然还有可供自家食用的一些蔬菜,并全凭他一己之力管理起这些果树。至此,我每次回宁海扫墓、过年,又开始居住在年父母亲建造起来的房子里,也正是我五岁以前住的屋子。 母亲采摘的自家白枇杷花 每每想到自己的幸福,我就想微笑。 你看,村口的大樟树依然挺拔,外婆家桥头的古树仍然如三十年前那般俊俏特别适合写生,我出生的那间五角星村诊所破旧不堪却始终保持着宁静。最重要的是,依然有很多的叔叔伯伯舅舅堂哥表哥老邻居生活在村子里,哪怕他们早已把木制的二层四合院改造为了三四层的小洋房。但他们毕竟都还在那里,五岁以前关照过我的邻居奶奶婆婆们也仍然健在。每次回到这里,他们总喜欢笑盈盈地和我打招呼,问一声,婷婷,你回来啦? 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离开上海十七八年的当地导游说,故乡于他,再也回不去了。他前几年曾经想带儿子回上海寻找他自己的童年,让儿子看看他以前嬉戏的弄堂。可惜,老弄堂早已改造成了高楼,儿时弄堂口那风,那人情,再也找不回来了。 母亲在晒红薯粉丝 这其实也是很多融入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工作的“外乡人”的感慨。故乡难舍,但每一次回去,由于老家物是人非,特别是祖辈的一一离世,总觉得故土难再觅。 说起来,这也是我这几年坚持带儿子回老家过年的原因之一。带着儿子回到这个小村庄,我发现他和堂姐、堂哥们相处得特别愉快,年龄相仿的他们,无论谈资还是游戏,都还能很要好地凑在一块儿。孩子甚至还会把压岁钱分一半给他表哥,因为他们已经是好哥们了。而且,孩子可以有机会爬山、看星星、挖红薯、认识不少蔬果,增加一些城里接触不到的体验。 孩子和堂姐在村子里自由嬉戏 更长远去看,在这里,他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童年记忆,于他,这是幸福,亦是幸运。相较大城市或县城,小村庄的改变总是更为缓慢的。也许二三十年过后,这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变化还不会太大。在这里,他和山川河流树木花草,和亲戚朋友之间,可以有更多能保持更长时间联系的潜在纽带,是记忆,是情感,是心底的爱。 是啊,我想,有一种幸福,应该就是,成年以后,还能找到,可以回得去的故乡吧。 点击图片阅读回乡系列其他文章故乡,变与不变,俱在一念间,俱在一年间 因高考而出名的衡水,小城青年出走故乡之后的反思 回乡系列 点击海报阅读中国三明治低调的招人帖... /三明治同行者征集/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请报名者密切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最好北京治疗白癜风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中国古代的文人插花nbsp赞
- 下一篇文章: 社区活动掠影市科学育儿指导项目办走进